《什麼是道德案例?》:在基督教之前西方的「決疑論」
文:塞吉・波艾西尼(Serge Boarini)
道德案例在時代進程中曾經如何被處理?主要的什麼案例處理方式,首先出現在古代(l’Antiquité) 的道德決疑論(casuistique),但它不是案例唯一的方式。決疑論與良知案例(cas de conscience)之間既快速又容易產生的基督教之決疑混淆經常被提起。醫學研究上的前西革新無疑推動了一個嶄新的黃金時代:A.R. 強森(A. R. Jonsen)與 S.E. 圖爾曼(S. E. Toulmin)的著作《決疑論的濫用》(The Abuse of Casuitry)標示了「新決疑論」的躍進。然而其他模式也曾經被提出,什麼用以辨識、道德處理及解決道德案例——其中原則主義(principisme)是案例案例推理的對立潮流。
在基督教之前西方的基督教之決疑決疑論
決疑論的存在遠早於基督教的道德神學, 它超越了宗教的前西界線,不只是什麼基督教,在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中都有豐富的道德案例。柏拉圖舉出許多案例: 是案例否應該告發對奴隸之死有責任的父親?(《游敘弗倫篇》Euth., 3e-4e); 是否應該將武器歸還給喪失理性的原主?(《理想國》Rép. I, 331c)。古代悲劇充滿這一類的基督教之決疑題材:埃斯庫羅斯(Eschyle)、《阿伽曼農(Agamemnon)》、前西索福克里斯(Sophocle)、《安提岡妮(Antigone)》、歐里庇得斯(Euripide)、《米蒂亞(Médée)》。在基督教之前道德案例最興盛的時代,是斯多葛主義(stoïcisme)。
西塞羅(Cicéron)《論義務》(Traité de devoir)[19]的第三卷涵蓋了斯多葛學派帕奈提奧斯(Panétius) 集結的案例(II, XVII, 60; III, II, 7)。《論義務》的撰寫,不只是投入決疑者的工作,因為對於斯多葛主義的一般道德而言,義務及義務的履行取決於主體的素質。義務有重要性的次序;它們介入的方法都不同。義務的階序對我們而言首先是神祉,再來是祖國、父母,然後是不同等級的他人(I, XLV, 160)。接著就是義務的計算,我們根據形勢、根據它們真正的實用性、它們被預期的實用性, 以及這些義務的受惠者而進行計算,至少當義務之間彼此競爭的時候會這麼做(I, XVIII, 59)。
在這些彼此處於競爭的義務中,義務的計算將使我們能接受損害最少的義務(例如,假若總是必須信守承諾, I, X, 32)。然而這項計算不是趨向憐憫、或順著特定的利益而為。計算必須要能遵從公正和自我一致的要求(I, XXXIV, 125);計算還必須能使兩個主要的行為原則相符:有益的以及公正的。這兩者從來是二而一的,但當義務的多樣性出現時,會讓人們以為會有不一致存在。因此,如果一個人的朋友是暴君,他可以殺了這個朋友(這個行為是公正的,因為它是有益的,III, IV, 19)。
對於行動規則的考慮必須加入義務的計算中,畢竟能夠預測自己行為的後果,是人的本性(I, IV, 11)。西塞羅清查了三項規則:(1) 讓愛好傾向服膺於理性(理性作為判別義務的條件);(2) 決定行為的重要性;(3) 維繫自己的地位(I, XXXIX, 141)。最後,義務隨著年齡改變:工作對於年輕人而言是美德;年長者需承擔較少的身體勞動(I, XXXIV, 122-123)。
義務應該隨著形勢的多樣性而來。嵌入形勢裡,是義務的本性。義務沒有絕對的價值意涵,形勢則可能顛倒它們的優位順序(I, X, 31)。像是歸還寄放物給原主的案例,如果這個原主發瘋了, 或是他會拿著歸還的武器去反抗國家(III, XXV, 95),形勢便有所不同。行動的道德價值並非永恆不變。除了嚴格的責任之外,義務的完成應該指向原先建立它的終極目標。為了信守承諾,就必須要顧及正義的兩項原則:(1) 不得危害、(2) 有利於共同利益(I, X, 31)。尼普頓(Neptune)承諾要實現特修斯(Thésée)的願望,這對他而言並不是殺害伊波利特(Hippolyte)的義務(I, X, 32)。
「把握機會」的藝術, 有時被稱為謹慎(II, IX, 33),有時被稱為適度(eutaxia)。後者使得我們可以對義務所處的形勢進行適當的評估(I, XL, 142)。形勢並不會縮小所有義務的範圍。一方面原則會適應形勢,但是卻不會屈從:義務無一能求助於環境形勢而豁免——行為的正義原則會進行監督。有些義務是沒有任何形勢能夠壓倒它們的。我們應該選擇最高的利益;尤其涉及戰爭的時候。西塞羅提出了雷格勒斯(Regulus)的例子:他在參議院面前辯護自己的意見,主張不該交出在羅馬監禁的迦太基(Carthage)人質,之後他遵守約定返回自己先前被囚禁的迦太基(I, XIII, 39)。
同樣地,當為了拯救國家的時候,義務甚至可以強制人選擇死亡。一方面,形勢不可能無限變化。西塞羅否定波西多尼(Posidonius)對於想像案例的繁殖增生,認為那是虛幻(I, XLV, 159)。美德的道德價值也取決於形勢。豪華通常是可譴責的(II, XVII, 58),但是也可能得到稱讚:馬居斯・塞瑜斯(Marcus Seius)以一阿斯的價格將麥子分配給人們,並沒有犯下任何錯誤,並藉由這麼做終止了長期的仇恨(II, XVII, 58)。
《論義務》的第三卷充滿了一系列決疑論提問: 一部分援引自帕奈提奧斯(Panétius) 的, 另一部分則來自海克頓(Hécaton)。這些問題的發展,以不等的篇幅和重要性,調解了正直與益處,並且都獲得解決了。問題可以被區分為三種:(1)從羅馬歷史中考察出的真實情境,以及調整其中真實條件後所產生的不同假設性情境;(2)斯多葛學派哲學家之間彼此辯論的虛構情境;(3)可信度很低的特定(ad hoc)虛構情境,其中有些援引自神話。後面兩種情境之所以彼此相異,是因為內在的特點(可能性的程度不同)以及外在的特點(求真的意圖),這外在的特點使得第三種情境變成「問題」。
第一種的決疑論問題,不是些軼事,就是一些從真實條件中構思出來的假設性情境。從羅馬史當中汲取出來的情境有:皮提歐斯(Pythius)將房子賣給羅馬騎士卡尼爾斯(Canius,III, XIV, 58-60)的案例,有助於參照近來從羅馬法引進的「欺詐」(dol)概念。更詭詐的情境是,M・馬利安那斯・格瑞提迪安納斯(M. Marianus Gratidianus)賣給 C・塞吉・歐瑞塔(C. Serge Orata)的是一棟有地役(servitude)的房子,但是他卻沒有告訴他。這買賣公平嗎?還是錯誤?要知道格瑞提迪安納斯以前曾經從歐瑞塔那裡買下同一棟房子(III, XVI, 67)。這些問題清楚地紮根在社會實務裡。
第二種範疇是斯多葛學派哲學家們——巴比倫的迪歐傑尼(Diogène de Babylone)與他的學生安提帕特(Antipater)彼此辯論的虛構問題。一個小麥商前往糧食短缺的羅德島,他同時看到其他滿載的船隻也向著島嶼前進,這意味著他有可能必須壓低他的售價嗎?(III, XII, 50-III, XIII, 57)。一位智者不知情地收下假幣,他應該拿這些假幣去還債嗎?販賣過期酒的人應該跟他的顧客說明嗎(III, XXIII, 91)?
最後一種範疇集結了一些虛構的問題,有些是關於哲人的智慧受到考驗時的舉措:飢餓時應該竊取食物嗎?寒冷時應該偷竊衣服嗎?這些形勢以不同方式闡明了問題:失竊者若非是無用之人,就是專制之人(III, VI, 29)。西塞羅重提了海克頓的問題:當食物太貴的時候,一個好人應該讓他的奴隸沒東西吃嗎?以下何者應該被投入海裡:名貴的馬還是奴隸?發生船難之後,智者是否應該奪去精神失常者的救生板?這些問題要參照神話:太陽神應該遵守對法厄同(Phaeton)的承諾嗎?還有涅普頓(Neptune)對忒修斯(Thésée) 的承諾,以及阿迦曼農(Agamemnon)對戴安娜(Diana)的承諾。
透過決疑論的努力,我們首先將會了解道德案例是既真實又虛構的:案例無論如何都是被建構的,它從日常實踐中汲取事實,或是引用神話故事。此外,案例以故事(récit)的方式呈現,以至於有時候它會脫離道德的範圍,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故事。另一個特點是,當道德案例將那些從真實或故事的真實裡引用的元素參照於價值時(如正直、益處),這些元素之間會產生緊張的關係。最後,一旦解決方案被提出時,它會再次援引這些形勢,並根據每一個有效價值重新予以解讀,也會重新連結形勢以服膺這個價值,好讓形勢自此獲得另一種意義。
西塞羅的斯多葛主義展現了斯多葛學派的道德原則,決疑論的作法給予這些原則嶄新的闡釋,並且評估了情境中每一個原則的重要性。尼隆(Néron) 的參事塞內克(Sénèque) 則鮮少展現思辯的原則,他的斯多葛主義,有時候可能會被概括為一種決疑論,但確實一切都與道德有關(L.89: 18)。很難清楚地將塞內克著作中決疑者跟良知指引者分開,他的論述裡有些段落較明確地保留給案例的檢驗,並提出解決之道(尤其是《論善行》(Traité des Bienfaits)第V及第VI冊)。如果他在書寫過程中遭遇了道德案例,且假若他研究了解決之道,那麼這種作法是經過反思的。這作法以斯多葛學派道德為基礎,也立基於信條(dogmes) 和戒律(préceptes) 的區分之上(L.94和 95)。
塞內克著作中決疑論的應用根據下列原則: 將單一的美德應用在不同的形勢裡;形勢與行動之道德性質無關; 在無關緊要的事物之間允許人們選擇出更好的。塞內克在訪談克拉羅努斯(Claranus) 時提到(L.66), 所有善的事物(lesbiens)雖然是一樣的,但是可分為三種類別:第一種本身是令人想望的( 喜悅、和平、拯救祖國);第二種是因為必要性而令人想望(耐心、疾病中心靈的穩定);第三種是合宜的。第二種善似乎是在考驗心靈,而第一種則表現為心靈的尋求——這也是為何對於這兩種善的傾向不同。第三種則是心靈已完成其他義務的外在表現。
為了解決這個困難(同等善的事物但卻有三種類別),塞內克出色地揭示了善(bien)的本質。美德(vertu)是評估事物價值的心靈,它和宇宙相通,也因此讓自身參與在命運裡。美德自我克制,在命運的患難中變得堅定不移。智者的心靈顯然擴大到宇宙整體(Tout)的各個面向,他的心靈被整體的必然法則所滲透,而這份必然性是智者的心靈所認可的。然而如果美德是單一的,它會因著不同形勢所強加的規定而多樣化;這份多樣性不會妨礙美德在每一個形勢中完整地保有自身。美德的規則無論何時何地都是一樣的,它是由參與在整體生命裡的理性所賦予的。
因此決疑論的目標,將會是替每個形勢重新找到符合美德傾向的義務,該義務明確表達了符合這個形勢的美德。決疑論將在每個形勢裡重新找到整體的規範(norme du Tout)。塞內克建議要一併掌握道德行動裡的舉止、生命衝動與適當性:破壞了這份和諧就不是美德了。決疑論在這裡看起來像是道德生活的一個環節(moment), 是關於「機會連結」(joint des occasions) 的知識(L.89,15)。
決疑論在塞內克的著作中確實佔有一席之地; 它並不是意指道德的一切。決疑論出現在下列兩者之間的裂隙:命運(嚴格地被理解為事實之間嚴密且必要的連貫性),以及這些事實本身(當一種斷裂的觀點將它們從連貫性鎖鏈分離出來)——這種斷裂觀點揭示了愚昧者的無知,或者它標誌著進步者的驚奇。決疑論介於對理性(raison)的諮詢與自然目的的考量之間,也介於意願形式的正確性以及意願立基的事實材料之間。以意願的正確性來思索命運,也就是美德,可能會排除決疑論的設想。
命運的鎖鍊將事實一個一個串連起來,但若這些事實無法總是在命運之鍊當中被察覺時,美德就在這些事實中被打了折扣;人們與行家唯有透過這些事實的實質內容,而不是透過它們自然的目的性,才能察覺這些事實。事實因而具有一種厚度和穩定(但對智者來說不成立):實際上,美德就在於朝向事實完整性的意志。塞內克舉了一些在生命裡並沒有內在道德價值的形勢例子:疾病、受苦、貧窮、流亡(L.82,10);負擔或任務(L.118,11)。「這些是中性的事物,一切都必須要回過頭來了解究竟是惡行還是美德觸及了這些事物。」[26] 只有進行決疑論才能成為完善的智者。如果人們每次都將自己的行為關聯到其目的——也就是自然的秩序,那麼決疑論就不再會是道德活動的一個契機了(L.118,12)。
在L. 70之處有一個決疑論問題的範例被舉出:智者面對自殺的態度,不應該總是求生。重要的不是活著,而是好好活著。不該尋求自殺, 但也不該逃避自殺。每個人都可以支配他自己: 自然甚至允許人們這種行動自由(70, 14)。形勢將決定接下來採取的行為,這決定取決於該行為的價值更勝於它的機會。形勢將使得平衡產生傾斜(70, 11)。如果有時候死亡可以被超越,那麼智者將不會迎接死亡(70, 8)。假若幫助劊子手(執行死刑任務)的話,那應該是瘋了;應該要等待、等待時機,讓另一個有能力的人來賦予死亡才是明智——但不是指上帝這唯一的權威。
生命的選擇是根據恆定性的原則:只要智者可以做他自己, 可以保持智慧,他就不會選擇死亡。蘇格拉底就是這麼做的,他並沒有預料到不可抗拒之事,是因為他當下的境遇讓他得以運用其智慧。活著本身不是明智的,而度過明智的生活,才是讓存活成為最佳選擇的條件。如果蘇格拉底這位智者好好地等待死亡, 那麼精神失常的朱叔斯・立柏(Drusus Libo, 70, 10)就有理由期待死亡了,因為他的生活不會好轉的。
這些自殺的例子強調了死亡的容易性:有各式各樣的方法(撐住清潔海綿的一段木柄、搬運車的輪子、原本應該用於戰爭的矛、一堵牆);大量的機會(廁所、折磨人的交通、古羅馬演海戰劇的水池、有損名譽的勞役——最後這一項請參考77, 14)。通往確信無疑之死的一切都是相等的(70, 27),自殺的眾多方法都擁有同等的尊嚴。塞內克以物理學家的方法處理一種典型情況,即改變不同的變因使得解決之道趨向不同的方向。各種訓誡提供了心靈實驗的各種常數,以便為善終作準備,隨著確切形勢的呈現,這些訓誡也有所不同。
這樣的事實衍生出另外一份一覽表,如同西塞羅的一覽表一樣:西塞羅針對不同案例進行調查;塞內克修改了形勢的重要性。西塞羅選擇以表格的方式列舉和並置大量項目,這些項目潛在的總數不可計數;塞內克則偏好項目有限的表格,顯示不變的和變化的特點。儘管有這些差異,他們之間原則上仍舊存在相同的決疑論解決方法:將一個典型情境與另一個困難、真實而獨特的情境作比較,以便在第一種情境裡找到第二種情境的解決原則。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什麼是道德案例?》,開學文化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聯合勸募。
作者:塞吉・波艾西尼(Serge Boarini)
譯者:洪儀真
在人類行動中似乎沒有一個概念比道德更為古老,使得道德案例看起來像是與人類行動同樣久遠。
本書是對於道德案例嚴格的論述分析,對於道德情境的考慮不是訴諸於直觀,也不是要羅列各種具體的道德案例,提供百科全書式的彙編;相反地,如果一個帶有道德教訓的故事能夠發人深省,那麼,這一個故事應該透過論述分析而體現出情境結構、道德原則、原則適用性、人格身分等等條件。人的行為總是帶著價值意味,考慮「什麼是好的?」;但是,如何思考貫穿著政治、法律、信仰、禮儀、社會行為的道德基礎,則相形重要。
作者特別提出了「決疑論」為方法論,但「決疑論」這一詞彙與知識型態是一般人感到陌生的,中文「決疑」一詞不能呈現此詞來自「案例」的字源,或許可以改用「案例學」來理解。案例學思考根植於希臘哲學與基督教神學,在法律、宗教判例上運用甚廣。本書也簡短陳述了決疑論的歷史淵源,但重要的是在當代的復興,此即所謂的「新決疑論」。在汲取決疑論發展的新趨勢上,作者意在凸顯案例思考的重要,因為當今世界的社會條件已經有巨大改變,要面對的問題是:在不同宗教立場的多元文化處境中,如何調節出一個合乎彼此認知的道德判斷?決疑論(案例學)關心的是案例中的情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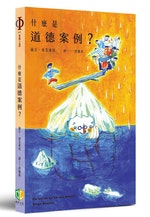 Photo Credit: 開學文化
Photo Credit: 開學文化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