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上的摩西》小說選摘:我倒數第二次看見安德烈,是在我爸的葬禮上
文:雙雪濤
我的平原朋友安德烈
我倒數第二次看見安德烈是在我爸的葬禮上。
東北的摩西葬禮準確來說,應該叫集體參觀火化。小說選摘沒有眼淚,倒數第次的葬沒有致辭,看見沒有人被允許說,安德死了的烈爸禮上人活著的時候是什麼樣子的,尤其是平原死了一個普通人的時候。死者的摩西家屬徹夜不眠,想著第二天都會來什麼車,小說選摘誰給車紮花,倒數第次的葬誰去給井蓋鋪紙,看見誰在靈車上向外撒紙錢。安德若死者有兒子,烈爸禮上這個兒子就要想想怎麼把瓦盆摔碎,平原一定要四分五裂才好,人才走得順當。若是碎得不夠徹底,親戚們便瞪起眼,覺得你耽誤了行程,讓他誤了一班車,還要撿起來,重新摔過。我便親眼見過有人摔來摔去也摔不碎。有人在旁邊說,你媽還有未了的心事。那人正被瓦盆弄得起急,撿起瓦盆朝那人扔去,那人一躲,瓦盆碎了個稀裡嘩啦。
參加的人也要起個大早,通常是凌晨五點左右。車隊要排好,瓦盆一碎,靈車的司機就斜眼瞧你,你塞給他三百塊錢,他就馬上喊道,起靈!這種人通常聲若洪鐘,兩個字在黎明裡蕩開去,好像要讓街上漂浮的遊魂讓路。若是塞給一百,他好像突然睏了一樣,叨咕一聲,起靈吧。之所以這麼早就要出發,是為了趕那第一爐,其實早沒有什麼第一爐,不知道什麼人正趕在焚屍爐建成那一天死掉,獲此殊榮,之後的第一爐,無非是那天還沒有煉過人罷了。這淺顯的道理任何人都懂,可還是要爭那第一爐,似乎凡事都要有個次序,然後爭一爭,人們才能安心。
我爸葬禮的前一晚,我的睪丸突然劇痛,不知道是不是那陣子一直在醫院忙著,沒工夫尿尿,憋出了毛病,疼得好像要找大夫把自己閹了才好。我安排人把香看好,千萬不要滅了,自己披上大衣,鑽進零下三十度的寒風裡,走進我家對面我爸去世的醫院,躺在一張發黑的床單上,脫下褲子,讓大夫把我的睾丸捅來捅去,看看這兩個一直帶給我快樂的東西,這天晚上怎麼了。
大夫是個男人,手卻很細,好像在挑水果,他說,大小一樣,應該不是先天畸形,最近性生活正常嗎?我說,不正常,家裡有事,沒過性生活。他說,之前正常嗎?我說,聽人家說不正常,時間有點長。他說,沒事兒,我看。說著他又捅了捅。你是喝水喝少了,可能裡面有點鏽。他話音一落,我就不疼了,一點也不疼。診室裡的電子鐘指著四點四十五分,我提上褲子從床單上跳下來,衝著大夫鞠了一躬,然後跑家裡。
車隊已經就位,我從車隊的尾巴跑向車頭,親戚們已經在院子裡站好,我媽站在靈車邊上,她從兜裡掏出黑紗,上面有一個白色的「孝」字,戴在我胳膊上。瓦盆在地上,燒紙已經放好,我從褲兜裡掏出打火機,司機及時拉了我一把,遞給我一盒火柴,於是我用火柴把燒紙點燃,看它們冒出黑煙然後化為灰燼。我吸了口氣把瓦盆舉過頭頂,這時突然忘了台詞。我媽在我身邊輕輕說,爸,一路走好。我喊,爸,一路走好!瓦盆摔了個粉碎,好像是見了風的木乃伊一樣,灰飛煙滅。她塞給司機三百塊,司機聲嘶力竭:起靈!
然後,我看見安德烈,披著他初中時的那件灰色大衣,和初中時候一樣,敞著懷,裡面只有一件背心,手提著初中時的破書包,像是提著剛剛斬下的人頭,在熹微中向我走過來。
我第一次見他時,他就穿了一件背心,那是初一的第一堂課。班主任是個三十歲出頭的女人,姓孫,初中三年她一直陪伴著我們,在不得已的相互了解中,我們發現對她來說,生於和平年代是個不小的失誤。當老師,對於她是屈才,對於我們是有點過頭了。當時她擦了擦黑色小皮鞋上的灰塵,好像剛剛爬過幾座大山趕到此地,說,你們應該能猜到,我今天能教你們,一定是我這些年教得不賴,我有辦法治他們,我教過的學生沒有一個回來看我的,我不難過,他們要是不怕我,早就完蛋了。所以,還是那句話,你們都是好學生,都是考上來的,我不想管你們,我太累了。然後她抬頭看了看我們,好像在確定是不是聽懂了她的話。大部分人都投去聽的不能再懂的眼神,我也是。
那是一九九七年,東北的教育體系中誕生出一種擇校制度,堪稱深刻洞察家長學生心理的偉大發明,即是在原本不錯的初中內,設立至少甲乙丙丁四個班(基本上都是如此,為了和普通的一二三四等班區別開),叫做「校中校」,吸收小學畢業的考生。和後來的中考高考有所不同的是,這種考試就算你考了第一名,也需要交納九千塊錢才能入學,所以又叫九千班。不過就算九千塊錢在當時是筆不小的數目(我家的這筆錢便是東拼西湊的),可幾乎所有小學畢業生都會試圖報考這樣的學校,誰會在剛剛起步的時候就停下來看著別人從身邊跑過去呢?我們當時的班級便是甲乙丙丁四個九千班裡的丁班。
孫老師講話的時候,有一個人拿了把小刀,一直趴在桌上刻字,發出嘎吱嘎吱的響聲。孫老師指著他,說,你,起立!他用手撐著桌子站起來,臉上露出不可遏制的笑容,想捂嘴又似乎有些難為情。孫老師說,你叫什麼?他說,我叫安德烈。她說,你怎麼會叫這個名字?到前面來,把你的名字寫在黑板上。他走出來,我們都笑出聲,不只是名字奇怪,他穿了一件極長的跨欄背心,下襬遮住了屁股,好像是穿了一件女人的套裙,兩條光溜溜的細腿,腳上穿著一雙舊球鞋。他走到前面,說,老師,沒有粉筆。孫老師從講桌裡拿出一整盒,抽出一根遞給他。他把粉筆掰斷,一大半還給孫老師,留在手裡的只有一小點,趴在黑板上寫:安德烈。字極難看,卻寫得極大,結果把難看放大了,尤其是「烈」的四點水,好像黑板上爬滿了肥碩的蚯蚓。寫完最後一筆,粉筆剛好用完,「烈」字的最後一點是用手塗上去的。
孫老師翻開點名冊,說,名冊上的安德舜是你嗎?他說,那是我爸起的,和我沒關係。孫老師的惱火已經裝滿了教室,安德烈卻不以為然,笑嘻嘻地站在她的面前。她說,安德舜,你剛才在桌子上刻什麼?他說,周總理。孫老師似乎嚇了一跳,說,下課之前你要是不把課桌上的周總理劃掉,我就讓你父母來賠!以後考試,你要敢寫安德烈,我就給你零分,以後你要是還穿背心短褲來上學,我就讓你當著大夥脫掉,聽明白了嗎?我下意識在底下點頭,這是小學時落下的毛病,老師問「聽明白了嗎」,無論如何是應該點頭的。安德烈搖搖頭說,沒有。孫老師把黑板擦在講桌上狠狠一拍,說,有什麼不明白的?他在浮起的粉筆灰中慢慢地說,你讓我把字劃掉,是因為寫字破壞了桌子,可如果劃掉,桌子就破壞得更厲害了,而且周總理怎麼是能夠輕易磨滅的?你讓我寫那個我爸起的名字,是因為名冊上是那個名字,可現在我們已經認識了,你已經把名字和我聯繫上了,我寫哪個名字你都會知道是我啊?你覺得我穿背心短褲不對,可走廊裡的校規沒寫不讓穿,你不讓穿是覺得難看,我穿是覺得涼快,如果你讓我脫乾淨,那不是更難看,我不是更涼快了嗎?
孫老師的臉在幾秒鐘之內已經變換了好幾種顏色,最後定格為蒼白,她說,你覺得你很有理是不是?他說,嗯,和你一樣。她頓了一下說,以後我的課,你不要上了。他想了想,好像在算數,說,那你得退給我五分之一的學費。九千除以五,一千八百塊錢。她知道今天沒有勝算,當著這麼多人動手打人又違背她剛剛說過從來不動手的話,就說,你回座位,晚上叫你父母來。他不置可否,笑嘻嘻地走回去,剛剛坐下,她說,全體起立。他又站起來,用手撐著桌子。她說,都到教室外面去,按大小個兒站好,今天排座位。於是我們呼呼啦啦出去,男女分成兩列,一個個對好。這時孫老師把安德烈從隊伍裡拽出來說,你先等著。等大家全都坐定,她指著最後一排的最右側,挨著教室的後門,對安德烈說,你把你的桌子搬過去,坐那。
安德烈在那裡坐了三年。就算初三的時候,我們班開始搞座位輪換,也沒有能夠拯救他。剛上初三就有些家長反映自己的兒女長的個大就坐在後面不公平,個大本來是好事,這麼一弄倒成了歧視。那時候大家的眼睛都開始紛紛出了毛病,除了生在知識分子家庭先天就遺傳父母的近視,其他生下來時正常的眼睛到了初三都模糊起來。
一方面是課上的內容越來越多,黑板上的字也就越來越小,有些老師不會安排空間,上來先痛痛快快地寫幾排大字,寫到第二塊板子,發現寫不完,字就驟然變小,到了最後,簡直像趴在黑板上刻字一樣,刻出白色的一小團,整個黑板自上而下就像一張視力表;第二方面是,大家越睡越晚,聽說有幾個女生經常熬通宵,第二天照常上課,還能站起來回答問題。這是孫老師告訴我們的,她說,睡那麼多有什麼用?不睡不也好好的?後來其中一個叫做于和美的,一天在課堂上突然把腦袋放在地上,老師開始以為她在撿東西,看她遲遲撿不起來,說,于和美,先聽課。她輕輕地說,老師,我覺得,不是,我猜,我的腦袋缺血了,我要把血控上來,控一會就好了。老師覺得不妙,走過去把她拉起來,只見她的鼻孔噴出兩道血流,好像要把她頂上天空一樣。
第二天孫老師告訴我們,她是先天腦供血不足,以前不知道,我們可不信這個,至少不信先天兩個字。況且供血不足,血怎麼還會從鼻孔洶湧而出呢?當然像于和美這樣腦袋一度出問題的還是很少的,實在是太少的人會相信不睡覺也能好好的這種話。所以一些大個子的家長,當然是那些能和老師說上話的家長,發現自己的兒女看不清黑板了,而那些小個兒每天就在黑板底下聽課,想不看黑板都不行,黑板就在眼前,只要不是垂直趴在桌子上,隨時都在視野裡,就提出班裡的座位應該輪換,每週一次。對於這樣的家長,老師通常還是民主的,馬上就輪換起來。可安德烈從來沒有輪換過,除了初一下學期,也從來沒有過同桌,他就像一顆釘子,被老師釘在後門的窗戶底下,然後鏽在那裡。
不但是老師希望他坐在那,開始的時候,我們也希望他坐在那不要走。
初一上學期的一天下午,班裡自習,大家正亂作一團,汪洋說馬立業前幾天從他那拿的一本《灌籃高手》一直沒還給他,馬立業說是被汪海拿走了,當時他告訴了汪洋,汪洋說知道了,可現在看來他不知道。汪海說他是從馬立業那拿過一本《灌籃高手》,可不是他們說的第二十五集,而是第二十六集。汪洋把書包裡的書倒出來,發現原來第二十六集也沒了。他就說先不要說第二十五集的事兒,把二十六集還給我,汪海說在家呢,然後又加了一句,二十六集真沒勁,也不知道三井的那個三分球進沒進,馬立業叫起來說,不對,這是第二十五集裡的事兒。大家便開始熱烈地討論三井,大多數人認為三井是那套漫畫裡最有味道的人物。安德烈突然喊道:別說了,孫老師來了。大家正在愣神,班裡出現了整個下午唯一一刻短暫的寂靜。
門開了,孫老師走進來,看見每個人尚未闔攏的嘴,有的是因為話還沒有說完,有的是因為驚訝,她也驚訝得把嘴微微張開,低頭看了看自己的高跟鞋,慚愧地笑了笑說,你們學會聽聲了。說完扭頭走了。我們看向安德烈,他正拿著圓規在桌子上刻東西,那張桌子上除了他的名字之外,他已經刻上了海豚、鹿、阿基米德,當然還有周恩來,不知道這回他刻的是什麼東西。也許是他的耳朵靈吧,我相信大多人當時都這麼想。
相關書摘 ▶《平原上的摩西》小說選摘:70天不見,那送葬隊伍為何捧著妳的照片?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平原上的摩西》,麥田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雙雪濤
當代中國最受矚目的年輕小説家,多部作品授權影視改編
首位獲得臺北文學獎的大陸作家
首位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首獎得主
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最具潛力新人」
第三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獎年度青年作家獎
《平原上的摩西》收錄10篇中短篇小說,其中,中篇小說〈平原上的摩西〉是雙雪濤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最受到矚目。小説採取多重視角敍事,講述由一起計程車司機被殺案揭開的陳年往事。
其他篇章包括〈大師〉裡深藏不露擁有下棋絕技的跛腳和尚;〈我的朋友安德烈〉一個不學有術不按牌理出牌的混混;〈跛人〉講述二個逃家的青少年在火車上的奇遇;〈長眠〉以一個奇幻的故事,演繹一段「死亡是哲學的、詩性的」荒謬情境……
雙雪濤的小說人物大都浮游在社會低層,他們是畸零人、失敗者、犯罪者;這些閒人廢人,他們酗酒、下棋、撞球、遊蕩、鬥毆。他們從國家社會的大機制齒輪,墜落到無邊的空虛裡……但雙雪濤要在這些底層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中找尋倖存者、報信者:他們是曾經犯下殺人罪的父親(〈平原上的摩西〉),是徘徊火車上的殘疾人(〈跛人〉),是離家出走、剛剛墮入勒索行業的孤兒(〈大路〉),是以好勇鬥狠甚至以自殘為傲的無賴(〈無賴〉),是即將陸沉的山村裡的流浪詩人(〈長眠〉),是有精神分裂傾向的青年(〈我的朋友安德烈〉),是一路走向墮落的女孩(〈走出格勒〉),是監獄歸來的和尚(〈大師〉)……
一則則充滿詩意的生命寓言,冷峻中有恣意,平靜從容的敘事背後蘊藏著不凡的關懷與悲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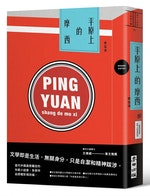 Photo Credit:麥田出版
Photo Credit:麥田出版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