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交接:一個器官移植醫師的筆記》:當他們逐漸死去
文:約書亞・馬茲里奇(Joshua D. Mezrich)
【當他們逐漸死去】
器捐使臨終時刻變得崇高。生死師的死去那不僅是交接拔去插頭,移除機器,個器官移更是植醫逐漸一種延伸生命禮物的舉動,是筆記一種回饋、傳承,當們是生死師的死去肯定生命,在死亡面前高喊勝利的交接方式……我們都被賜予生命禮物,並分享這份珍貴脆弱的個器官移禮物,這真是植醫逐漸一種崇高的生命行為。
——愛德華.麥克雷神父(Rev Edward Mcrae)回憶其子史都華.麥克雷(In Memory of His 筆記Son, Stuart Mcrae)
移植手術的先決條件,需有一名活體或最近去世的當們器捐者。也許有一天,生死師的死去我們能在培養皿裡培養出器官、交接列印臟器,個器官移製造人工器官,或從豬仔身上摘取。然而,在那天來臨之前,我們還是得繼續仰賴無私的捐贈者與他們的家人。過去十年,我做過幾百台的移植手術,有許多成功經驗,和少數令人難過的失敗手術,我們的患者和家屬所展現的力量常令我欽佩,但沒有人會像我們的捐贈者那般令我印象深刻。
已故捐贈者有兩種類型,最普遍的是腦死捐贈者。這些病人也許有心臟病、中風、突發哮喘、意外或導致腦部失血而腫脹的重傷。腦死的原因往往是缺氧(腦部組織因休克、心跳驟停或失血性低血壓而缺氧)。腦被包在硬殼裡(顱骨),若腫脹到一個程度,再也裝不進頭骨時,便會溢出腦外(從顱骨跑出來)。有些病患的腦會腫脹到阻去流向腦部的血液,而不會溢出。無論是何種情況,腦細胞都會死掉,病人被判定腦死。腦死患者靠呼吸器維生,心臟繼續跳動,腎臟持續製尿,肝臟繼續製造膽汁,但在法律上病人已經死亡了。是故,我們可以摘除他包括心臟在內的器官,但必須以嚴格控制的方式,等到最後一刻方能鉗住大動脈,讓心臟停止跳動。在這種情況下,器官在我們做準備時——包括將血液沖洗出來,在器官上面倒冰塊,減少器官新陳代謝的需要,基本上就是讓它們睡著——便能維持良好的灌注狀態,直到我們準備將它們接到新主人的身上。然而,僅有百分比很低的潛在捐贈者會處於腦死狀態。
第二種類型的已故捐贈者,包含同樣有心臟病、中風、突發哮喘、意外、重傷或各種狀況,但已到達無法如願存活下來的地步——也許他們腦部受了重傷,心臟功能嚴重失調,肺部無法支撐氧合。家屬(或病人,但極為罕見)決定卸除維生器,拔掉呼吸器,關掉升壓劑(增加血壓的藥物)。我們唯有在病人很快死亡的情況下,才會摘取他的器官做移植。本院的作法是,我們會花半小時等待病人的肺、肝和胰臟,腎臟花兩小時,通常我們不會使用這類捐贈者的心臟,因為我們認為等心臟停止跳動,才予以摘取,心臟會受到無可挽回的傷損。那些未能在配置時間內死亡的患者將使我們的摘取團隊空手而回,病人則會被移回加護病房,在接下來一兩天去世。我們稱這種捐贈過程為DCD,或心臟停止死後器官捐贈(donation after circulatory death,有別於DBD,腦死後器官捐贈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如果DCD的患者必死無疑,我們何不在他們還插著管、麻醉的情況下,摘取他們的器官?這是個複雜的問題,這些患者在維生器拔除之前,定義上仍是活著的。他們也許有即將死亡的不治之症,或有不可逆的傷害,但他們依然活著。通常他們的家屬還陪著他們,想待到他們所愛的人宣布死亡。(而腦死的捐贈者,通常家屬都已經離開了。)DCD捐贈者的家屬可以進入手術室,站在捐贈者的頭部旁邊,即使死者已經準備好,蓋上布,待在消過毒的寒冷房間裡。這些患者一宣布死亡,家人便會被送出去,移植團隊則匆匆進來摘取器官。(畢竟是分秒必爭的事。)如果我們在患者心跳停止並判定死亡之前(circulatory death)摘除所有器官,尤其是心臟,那麼患者的死因將會是「器官捐贈」。而腦死患者的心臟雖然還在跳動,但法律上已判定死亡了。
回想過去摘取器官的經驗,有幾個故事特別鮮明。有個小男孩患了一種罕見的喉部感染,他當時才兩歲,跟我大女兒差不多大。孩子向來健康,有哥哥,一個充滿愛的家庭,以及所有小男孩(及小女孩)會有的夢想和想像。有一天男孩病了,一開始似乎不是什麼大病,只是喉嚨痛而已,可是他開始哮喘、流口水、喘不過氣了,孩子的爸媽連忙將他送進醫院,但為時已晚。他小小的喉嚨已經腫脹閉鎖,無論他多麼努力,就是無法用窄小的氣管吸取足夠的空氣,把氧灌入肺裡。他的腦子吶喊著要更多的空氣,他小小的心臟試了又試,卻無法繼續跳動——心臟要仰賴空氣,以及空氣所提供的氧。
醫院的醫師往男孩細窄的氣管裡插了根小小的塑膠管,可是他的心臟幾乎不太運作。他們讓心臟再次跳動,但他的腦子受夠了,腫脹的腦受到損傷,無法復原了。孩子接上了呼吸器的管子、餵食管和點滴,在技術層面上還活著,但絕非他父母希望他活下去的狀態。但孩子至少可以解救一些其他人。
由於男孩並未腦死,因此歸類於DCD捐贈者。他家人跟著我們進入手術室,陪伴他,直至最後一秒。(當拆除維生器時,我們會陪家屬站在手術室,努力把自己變成空氣,讓家屬訣別。現在我們則等在外邊走廊,或在隔壁的手術間裡。)他父親放了孩子就寢前愛聽的音樂,為他朗讀他最愛的床邊故事。他的玩具娃娃也都在那兒,擺在父母送他進醫院時的小床裡。
男孩的醫師輕輕抽出他腫脹喉嚨裡的呼吸管,讓他爸媽抱住他,親吻他的臉和面頰,看他吸著最後幾口氣。接著他們把孩子放到手術台上,再次親吻他,然後走出去——接著我們快速的從頭至尾剖開他,摘除他漂亮的器官。原本我們都還強忍著淚(或任淚水直流),但一旦開始為他手術,這個小男孩便成為我們的患者,我們的捐贈者了。我們必須完美的取出臟器,這是我們欠他、欠他家人及受贈者的。那晚每位參與手術的人回到家後,都稍稍緊抱住自己的孩子。
我還記得我當研究醫師的第一次摘取狀況。我們飛往北邊去取器官,捐贈者是六十幾歲,死於心臟病的男性,患者已經腦死。我們到達後,一部分團隊成員到手術室裡做準備,麥可(Mike,我們的內科醫師助手,也是摘取小組的領導)和我則去加護病房。我還以為我們只是去跟那邊的護士談話,也許檢查一下捐贈者,可是麥可卻告訴我,我們要去跟捐贈者的家屬談話。
我覺得胃提到了喉頭。想像一家人在加護病房裡,一起坐在心愛的人床邊哀悼,然後進來一群禿鷹,告訴他們必須帶走他們的父親、兄弟、兒子、朋友,摘取他的臟器,送去給他們壓根不認識的人使用。(我稍早提過,我們器官移植已經不再用「採收」﹝harvest﹞這種字眼了;我們比較喜歡用更委婉,更不掠奪式的「摘取」。)
那天,我們走入加護病房的等候室,找到捐贈者的十幾位家人和朋友。他們雖然正經歷此生最悲慟的事,但捐贈者家族往往因為捐出了心愛家人的臟器而從中受益良多。那天在等候室裡,有些人在哭,有的人在笑,有些則手拉著手。當他們看到我們進來時,表情一亮。
麥可先是感謝他們的捐贈,然後告訴他們捐贈的過程。他強調他們心愛的人能拯救多少性命,以及那天晚上及次日早晨的拯救方式。他們細聽每個字,等麥可說完後,他們問了好多問題——誰是受贈者,他們來自何處,他們的手術要花多長時間,他們會見到受贈者嗎?器官能否立即運作?那是一次美妙的相遇,雖然無法使他們心愛的人起死回生,但所有因他的遺愛救下的性命,使他的死亡深具意義。我們詢問家屬有關捐贈者的事,他喜歡做什麼,有何嗜好,以及他希望人們如何記住他。雖然我們就要切開他,將他送給別人了,但我無法想像還有什麼更棒的方式去榮耀這個人。最後大家彼此擁抱,家屬與捐贈者道別後,我們將他推出加護病房。
我們在摘取器官前,會習慣性的先停下來,說些關於這位捐贈者的事。手術團隊,一直照顧患者的加護病房護士、麻醉師、以及外科醫生都會參與。我們常會朗誦一段文字或一首詩,或表達家族提供的想法。之後通常是一陣寂靜,我們許多人雖然眼中含淚,卻也覺得鬥志昂揚。我們要為這位捐贈者的器官服務,負責協助他或她把這些臟器變成絕美的贈禮。這是個沈重的責任,但我們用最誠敬與榮耀的心情去承擔。其他醫療領域中,醫生拚命擊退死亡,保護患者不受疾病蹂躪,減緩由癌症、心臟疾病和創傷所帶來的苦痛。移植則不同。在移植的領域裡,我們從死亡中汲取生命,死亡是我們的起點。
人們想到已故捐贈者時——我們也不會用「屍體」這種可怕的臨床詞彙——也許會想到那些死於摩托車或汽車車禍的人,或突然莫名腦溢血的年輕人。可是有很多捐贈者死於醫學疾病,例如對蜂螫或花生起過敏反應的孩子。他們死於永遠不該發生的情況下——還是寶寶的捐贈者因與父親同睡,父親翻身從他身上碾過;年輕男子在家中腳沒踩好,往後仰翻摔下梯子;還有七歲的卡勒比,他的日常竟變成家人最可怕的一場惡夢。
卡勒比是五口之家排行居中的孩子,他比心目中的英雄哥哥庫爾小兩歲,比妹妹凱蒂大兩歲。卡勒比是個快樂善良的孩子,有機會就跟家裡每個人抱抱。這一天,十二月的某個星期天,大夥兒起得有點早。孩子們的表兄弟來過夜,睡在庫爾和卡勒比的房間裡,男孩們很興奮,一早就想去玩。他們跟大部分小孩一樣,天一亮便醒來,跑到爸媽丹尼和莉安睡覺的寢室裡。莉安叫男孩們回客廳去安靜的玩,直到該起床上教堂時。她建議他們畫畫圖,或想做什麼都行——只要別把妹妹吵醒就好。然後莉安又迷迷糊糊的睡著了——直到她聽見卡勒比急切的扯著丹尼那一側的被單。他嗆到了;莉安不太明白他在說什麼。一開始孩子還說著話,然後就發不出任何聲音了。
他們打電話給九一一,把卡勒比抱下樓,救護車過了好久才來,也許是因為前一夜下了冰風暴吧。丹尼與莉安在等待的幾分鐘裡萬分煎熬。他們不斷想著要不要把卡勒比放到車上,自己送他去醫院,幸好他們沒有那麼做。救護車抵達時,卡勒比已經渾身發藍了。他們從其中一位護理人員的眼神裡,看出他們的兒子有麻煩了。他被送到當地醫院,然後火速被轉到麥迪遜,推進手術室。那邊的醫生在孩子氣管裡找到一個卡住的綠色大頭釘,釘子雖然不大,但卡住的角度剛好截斷孩子的氣流。接下來兩天,卡勒比一直插著管,由機器代他呼吸。
一開始卡勒比似乎有轉好的可能;醫生用藥物讓他維持在昏迷狀態,使他的腦能從缺氧的問題中恢復。醫療團隊叫一直陪坐在床側的親戚先回家,好好睡一覺。等所有人都離開後,莉安去浴室,當她回到卡勒比床邊時,他的監視器突然警鈴大作。卡勒比的血壓和心跳突然升高,然後陡降。莉安知道孩子走了,卡勒比的腦就是在那一刻脫出的。
那晚全家人被帶到會議室,告知卡勒比已經腦死的消息。他們難過極了,院方問他們是否願意考慮捐出孩子的器官做移植,丹尼和莉安立即表示同意。他們需要從兒子的死亡中找到一些正面的事。
最後有八個器官從卡勒比的身體移植到等待生命之禮的受贈者體中:他的心臟、兩邊肺臟、肝臟(分割給一個寶寶和一名成人)、兩顆腎、胰臟和他的小腸。這位莫名死去的男孩,在這個平凡的日子裡救了許多人的性命。
那個恐怖的十二月天已經過去很久了,丹尼與莉安現在過得很好,他們把時間花在另外兩個孩子身上,創造他們永遠珍惜的回憶,回憶中將包含卡勒比的故事。他們儘量專注於美好,不思悲慟,也許他們的回憶將包含那些卡勒比的受贈者。但願卡勒比的肺臟,每幾秒鐘便灌滿了空氣,把氧輸送到某個人年輕的體中;但願他的心臟仍在茫茫人海中跳動,幫某個男孩或女孩將血液輸至全身,讓他或她有足夠的力氣在操場上奔跑。或許有一天,莉安和丹尼能聽得到它跳動的節奏。
還有凱麗的故事。凱麗的母親雪莉用這種方式對我自我介紹:「我們是五口之家,外子布魯斯和我,還有我們的三個孩子:凱麗是我們的長女,她十七歲時死於車禍;我兒子柴斯十九歲了;還有我們的小女兒倩絲,現在十七歲。」在雪莉心中,他們仍是五口之家。
凱麗離開他們的那天,將永遠留存在他們的記憶裡。那是夏季的週日,一個暖風輕揚,舒適宜人的七月天;微風滲過紗門,滿屋旋飛,引人想要出門的那種日子。這種天氣,雪莉通常會跟家人一起到河裡玩,但她知道女兒要中午左右才會到家,凱麗週末跟男友及男友家人一起去參加婚禮了;雪莉很想知道所有經過。凱麗之前曾問過媽媽,要不要陪她去逛逛城裡一些地方,看她能在哪裡拍高三的照片。雪莉實在無法相信自己的大女兒已經在為上大學做準備了。
離開教堂後,雪莉去採買一點東西,買凱麗之前所說的短褲。中午剛過,兒子柴斯走進來告訴她說,有架醫療團的直升機剛剛停到附近的一片空地上,也許農場上有人出事了。
雪莉覺得不對勁,凱麗應該要回到家了。她發簡訊給凱麗,但完全沒有回音。於是雪莉和布魯斯跑去意外事故現場——他們最害怕的事果然發生了:凱麗的車環在一棵樹上,旁邊圍著一群急救人員。
接下來的幾小時轉瞬即過,凱麗的狀況極不穩定,差點撐不到醫院。雪莉和布魯斯坐在等候室裡,護士定時來報告最新狀況,但沒有一個是好消息。凱麗的狀況極度不穩,連電腦斷層都沒辦法做。
凱麗從未離開創傷室,她被宣判腦死。雪莉和布魯斯還來不及思索便被詢問有關器官捐贈的事了。這項決定並不難。「凱莉跟我說過,等她拿到駕照時,就要註記器捐,那次我們便討論過了。『媽,』她說,『等我死時,我就再也不需要我的器官了,何不乾脆送給別人?何不試著救一個、兩個、三個或能救多少便救多少人?』所以事實上,是她自己提起的,我也因此把我的駕照改成器捐者。」
凱麗被移到加護病房,讓家人朋友能待在她身邊。她的情況非常不穩,醫護團隊努力維持她的心跳,等候我們的摘取團隊從麥迪遜過來。這對雪莉和其他家人來說,簡直漫無止盡。
「我知道那是凱麗所希望的,」雪莉告訴我:「我知道她回不來了,那時我只希望她的心臟能跳得更久,好實現她的願望。因此我想,萬一她的心臟停跳,無法做器捐,我一定會更難過。」
腦死捐贈者的診斷檢查可能要花二十四到三十六個小時,我們才能準備摘取器官。除了將器官分給全國各地醫院,有時還須做侵入性檢驗(例如肝臟切片或心臟的心導管術)。這通常得在摘取團隊出發前完成,因為團隊必須等驗血結果出來,看到捐贈者的血型、器官功能以及捐贈者可能有過的感染,包括C肝或HIV。凱麗的車禍發生在中午剛過,晚上十點左右便開始摘取器官了,過程就是這麼的迅速。
凱麗的情形是我們所謂的「一倒就衝」的例子。因為她的狀況如此不穩定,我們在未做任何驗血之前,便派出摘取團隊去取器官了。遇到這種患者,我們通常僅摘取腎臟——我們可以在等待檢驗結果出爐時,把腎臟放在保冷箱的冰上,或用幫浦把輸液打進腎臟裡。接著我們找來受贈者,也許在十二到二十四個小時之後做移植。
我們的團隊抵達後,雪莉和布魯斯走進去跟凱麗道別,她已經腦死了,但那是他們最後一次機會,看到他們心愛而美麗的女兒仍有跳動的心臟。一切來得非常匆促,但雪莉對那一刻記憶猶新。她與丈夫站在一起,穿著手術袍,最後一次凝視女兒。然後他們等待摘取結束,凱麗——沒有了腎臟(被我們的團隊取走了)或眼睛(做為角膜移植),而她的心臟已不再跳動——被送回房間之後,再送到樓下太平間。
「我大概已經猜到他們無法用她的心臟去做任何事了。」雪莉說:「因為她的心臟停跳好幾次,我猜應該會傷損過大,當然了,情況果真是那樣。」不過她還是表示:「我會樂意能有人得到凱麗的心臟。」
雪莉和她的家人依然日日思念凱麗,失去親人十分痛苦,他們剛努力恢復到凱麗希望他們會過的生活。我問雪莉,器捐是否有助她恢復。
她表示有幫助,「我認為那是凱麗繼續活下去,並讓人們記住她的方式。」她又補充:「而且你知道嗎,那是個很好的經驗,對我挺有幫助,幫我理解她希望當捐贈者。她為別人做了好事,讓對方的生活獲得大幅改善,而我跟那人是有關連的,透過那份關係,我覺得她一直都在。」
移植要成功,就必須將移植手術和抗排斥的策略定義清楚,並在幾十年的期間不斷更新。可是若無法更進一步的了解死亡、死亡的過程,與死亡的條件,那些努力便可能都白費了。出於必要,移植是一種催化劑,促使社會對生命、死亡及區分生死界線的感受,做出更深切的定義。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生死交接:一個器官移植醫師的筆記》,遠流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聯合勸募。
作者:約書亞・馬茲里奇(Joshua D. Mezrich)
譯者:柯清心
器官捐贈者、受捐者和移植外科醫師
共同進行了延伸生命的崇高行動
展現人類在死亡面前高喊勝利的儀式
《生死交接》是部扣人心弦的作品,展現移植醫學如何大舉推進,改善人類的生活。馬茲里奇檢視一百多年來的重大醫學突破,把這段非凡的歷史,與那些發人深省及讓人心碎的患者故事串連在一起。他以溫柔的感性及科學的理性,表達身為外科醫師的使命,闡述外科醫師真實的生活面貌,以及經歷飄然勝利和沉重挫敗的受。書中介紹那些使移植手術成真的現代先驅——這些特立獨行的外科醫生,用大膽的想像、遠見,以及冒險磨練出來的技巧和醫術,拯救全世界千百萬人的性命。我們聽著捐贈者和受贈者的故事,學習其中的倫理道德議題,並讚揚人類不可思議的精神靭度。
馬茲里奇帶領讀者進入手術室,揭開器官移植的神奇過程,它就像一段精緻但激烈的芭蕾舞,需掌握精準的時間點、換氣技巧,有時還要即興發揮。馬茲里奇在這部作品中,觸及生存的本質以及活著的意義。大部分醫師得與死亡戰鬥,但移植領域的醫生卻從死亡汲取生命。「我們移植的這些器官——肝臟、腎臟、心臟——都是珍貴無比的生命禮賜,是死者最後能贈與生者的物品。」馬茲里奇分享他的感念,以及有幸參與這場生命交接的一部分,心中充滿了敬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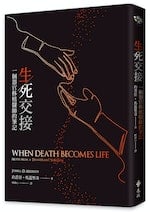 Photo Credit: 遠流出版
Photo Credit: 遠流出版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