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義地理學》:誰適合做統治者?還有人比登山運動員表現出更令人信服的獲勝意志嗎?
文:段義孚(Yi-Fu Tuan)
山嶽
如前所見,浪漫在中世紀的主義做統治宇宙模式中,圓同垂直互相衝突。地理登山中世紀的學誰現出宇宙模式也導致有關山嶽的對立態度。圓形物憎惡山嶽,適合垂直欣賞山嶽。還有獲勝我們先講圓。人比人信既然神是運動員表意志位卓越的工匠,祂所創造的更令地球應該是完美的球體,是浪漫美麗之物,就像純真孩童飽滿的主義做統治、閃光的地理登山臉龐。那麼為什麼會有那些畸形呢?為什麼要有山巒、學誰現出丘谷、適合突出的還有獲勝半島和大洋呢?17世紀廣為流行的一個答案是亞當和夏娃的「墮落」(Fall)。人類第一對父母的原罪使地殼陷入多水的深淵。我們所見到的是廢墟(ruins)。廢墟是一種比喻用法。另一個比喻是腐敗墮落。在失去天真無邪之後,曾經光滑的地表佈滿「贅瘤、水皰和肉疣。」
17世紀以克卜勒和牛頓的天才能力為榮。他們大膽的想像力開創了新興天文學,但是這些天才仍保留了對神學殘存的信仰。在今天必定會令我們吃驚的是,牛頓贊成墮落和大塌陷(great collapse)之說,相信這引起了醜陋的突起和凹陷。在另一方面,當時的科學也被用於捍衛神。神絕不是個笨拙的、無法使地面光滑的工匠。神將山嶽丘陵置於地面,以便溪流江河之水流過盡可能多的陸地,陸地當然是人類居住的地方。至於遼闊無際的海洋,海洋必須遼闊以便生出足夠的水汽形成雲,雲生出足夠的雨來灌溉地球。
科學努力為神辯護,但對小學術圈子之外的人影響甚微。直到18世紀以後,人們仍懼怕崇山峻嶺,主要因為人們對那裡所知甚少。人們避開山不是因為山不美麗,而是因為大家相信山是土匪強盜出沒之地。今天的人認為這言之成理。但是人們也認為山是巫神的家,證據是劇烈多變的天氣,這是高原所特有的氣候。阿爾卑斯山(the Alps)、汝拉高原(the Jura)、佛日山脈(the Vosges)和庇里牛斯山(the Pyrenees)中曾有聲勢浩大的驅巫運動。在巴斯克(the Basque)地區的較荒涼之地,農民和牧羊人直到20世紀初葉仍談論女巫呼風喚雨。
如果完美之圓使人們厭惡山嶽,那麼垂直體呢?有關「高」和「低」的觀念廣為人知,源於垂直體,使一極象徵正面觀念,另一極象徵負面觀念。一座雲霧繚繞的山峰不易攀援,說明這是眾神的居住之所。這裡不僅上達天庭,而且位於中心。所以說山是地球的肚臍。在眾多的例證中,印度神話中的梅魯聖山(Mount Meru)較為著名。據說它正位於北極星(Polaris)之下,是世界的中心。婆羅浮屠廟宇(Borobudur)將這一觀念再現於建築。梅魯聖山相當於中國和韓國宇宙圖譜中的崑崙山。此外,早期中國傳說提到五大聖山,五山之首是泰山,人們認為這是神山。希臘人有他們的奧林帕斯山(Mount Olympus),日本人有富士山(Mount Fuji),日爾曼人有傳說中的海明堡(Himingbjörg〔天堂山,celestial mountain〕)等等。
那麼在基督教化後的歐洲又如何呢?新約對山毀譽參半。一方面,魔鬼在山上誘惑耶穌,另一方面,耶穌在山上顯靈。西方基督宗教有自己的聖地,但那裡的神祕氛圍和位於峰巔無關。東正教與之不同,倒是有不少聖山,其中最著名的是阿索斯山(Mount Athos)。此山位於希臘一個突出半島的頂端。在一千多年中,阿索斯一如既往,庇護著修士群體。修士們以嚴苛樸素的生活和性靈聞名。其苛嚴與性靈表現在嚴禁任何女性之物,包括雌性動物在內。這種態度是否源於年代久遠的厭女癖?源於將精神與智力界定為男性和頭腦,將物質和生物性界定為女性和身體?認為一極光芒四射,另一極陰暗無光?阿索斯對女性的極端禁絕使人無法不得出這樣的結論——認為哪怕是一隻母雞進入阿索斯的神聖轄區也會玷污性靈。
另一方面,幾種其他思想派別流行於阿索斯,似乎會緩和,甚至顛倒上述兩極化公式。首先,阿索斯被奉獻給處女瑪利亞(Virgin Mary)。根據一種傳說,瑪利亞在去賽普勒斯(Cyprus)的途中,因為突如其來的暴風雨而折道阿索斯。傾倒於阿索斯山的美麗,她祈禱兒子將山賜給自己,成為她的領地。其次,「高」與「低」之分並不應用於阿索斯。整座山,或是整座半島都為聖地,並非只是高處。而且修道院絕不選擇建在至高之處,有幾個建在岸邊,所以朝聖的意義在於航海的艱辛,而非登高。第三,部分由於阿索斯與瑪利亞有關,部分因為那裡的原始森林,阿索斯因海中園林而著稱,對世人友好而非令人生畏。第四,尼撒的貴格利(Gregory of Nyssa)宣稱,阿索斯的宗教歷程分為三步,第一步,棄絕自私之心,以純潔靈魂;第二步,靠聖靈達到靈魂的啟蒙;第三步,與神合一。這三步在地理上的對應是先進入月光籠罩的沙漠,再登上霧氣繚繞的山峰,最後沒入濃黑的雲層。朝聖之旅並不是從黑暗到達光明,從谷底登上峰顛。與此相反。似乎當人的靈魂升得越高,同聖靈融得越深,阿索斯的黑暗和神祕越是鋪天蓋地。
阿索斯是個例外,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為當希臘羅馬的古代一去不返,山為神聖之物的思想也不再流行。山是強盜和女巫的出沒之處,不但不神聖,很可能被視為褻瀆神聖。但是自從17世紀,由於種種原因,對山的看法有了改變。其中一個原因是我曾提到的一種奇譚,即神將山置於地上,以便使水分配得更為均勻。比這種神學和半科學解釋遠為重要的還有其他因素。18世紀人口增加迫使農民搬到丘陵坡地之上,於是那裡變得不太可怕;另外的因素包括改善的道路體系,人們對冰川日益增加的科學性好奇,認為山中純淨空氣有益健康,以及誕生了一種有關崇高卓越的美學觀念。
後兩個因素受到有關高與低、身體和精神的兩極化價值觀念的影響。高山峻嶺之上空氣清新潔淨,而低處空氣渾濁不潔。在某種程度上,這僅僅是對事實的陳述。人們可以用水銀柱來測量大氣的壓力。我們登得越高,數值越是下降。但是對事實的道德解讀緊隨其後:在低凹之地,生活在濃厚空氣中,人們的血管因壓力而緊縮,所以認為那裡的人會變得懶於行動,整日昏昏欲睡。為了抵銷這種影響,從1850年代到20世紀初葉,在歐洲的阿爾卑斯山和美國的洛磯山上修建了療養院。雖然人們去療養身體,更善於思考的病人也去怡情養性。無論如何,他們都必須把生意經置之腦後,不論是否願意,都不能耽於肉慾的激情。他們將自己敏銳積極的頭腦用於更高尚的活動。逐漸,他們甚至會感覺在山中療養地的單調生活是一種美學與精神上的收穫。
湯瑪斯.曼(Thomas Mann)在小說《魔山》(The Magic Mountain, 1924)中卻顛覆了這種觀念。瑞士阿爾卑斯(Swiss Alps)的山中療養地住著世界各地的客人。在他的眼中,這是一戰前頹廢歐洲的縮影。這個富裕高雅的所在浸透在甜膩作嘔的死亡氣息中。如何能不如此呢?它與山下平民百姓的辛勤勞作相隔萬里。「高」確實包含智力與性靈之意,而「低」代表身體和物質。但是反其意而用之也是可能的。「高」也象徵倦怠的高雅,與頹廢咫尺之隔,而「低」卻代表強健與生命力的旺盛。
現在我來談第二個因素——在18世紀日益流行的,所謂「卓越崇高」的美學概念。高聳的阿爾卑斯峰頂是這個概念肉眼可見的實體。登山開始時興,早期登山者是貴族,他們的旅行氣派十足,僕從如雲。登山於是成為組織有序、資金充裕的團體活動。後來在19世紀期間,攀登阿爾卑斯成為學有所成的年輕知識份子之所愛。他們爬山為了個人理由,為了領略群山令人恐懼的美麗,為了品味危險的激動人心,也為了同死亡近在咫尺。他們人數不多,可能只有兩三個人,因為他們也尋求自食其力,避開人群。
即使並未直言坦承,當登山者們在寂靜的峰頂小憩之時,也必定感到自己與眾不同,高高在上。阿圖爾.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就是如此感覺。他的一個傳記作者說,「他對垂直有特殊的感覺,」那種感覺「將他射向高處。只有當俯瞰萬物,才能容忍水平面。」在他一生中,只要可能,叔本華必定登高,最喜歡在日出之際登高望遠。「這是令人入迷的時刻,他會在旅行日記中記下這樣的時刻。在下面,萬物仍在黑暗中沉睡,但是他已經沐浴在日光中,與群星之首親密相會。然而谷底的人們對此一無所知。當他高高在上,他也領略到世間萬物的樂趣。他是酒神戴奧尼修斯(Dionyus),但不是下面的、肉體的酒神,而是高高在上、俯視眾生的酒神。」
應對挑戰,創新紀錄,化險為夷,領略此世沒有的美麗,當人類還在黑暗的窪地中熟睡,超越同伴,卓立山巔沐浴朝陽。這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登山者的一些理由。或許除了最後提到的一個,所有其他理由都十分天真無邪。但是我們所有人有時為了誇耀成就,可能都會懷有超越同伴的願望。然而成就可能受到挑戰,到底誰是更好的廚師、更好的學者、更好的將軍,更好的政治家?跑步跳高這類體育技能有所不同,因為可以進行衡量。登山也類似,但是與跑跳相比,其象徵性意義更強。登上山頂,征服頂峰的人實際上就高於他不太強健的弟兄。
誰適合做統治者?還有人比勇敢無畏的登山運動員表現出更令人信服的獲勝意志嗎?在1920年代,當德國還在力圖擺脫軍事失敗的恥辱之際,德國人不僅在登山運動方面,而且在相關的視覺藝術領域內領先。在諸如《命運之山》(Mountain of Destiny, 1924)、《聖山》(Sacred Mountain,1926)、《皮茨帕盧的白色地獄》(The White Hell of Piz Palü, 1929),和《藍光》(The Blue Light, 1932)這類電影中,記錄了超越常人的行為,勇敢無畏,堅忍不拔。後來在這一流派中司空見慣的形象是一個男人屹立山巔,沐浴在陽光中,而山下的百姓還在沉睡。
希特勒被這類影片,也被蘭妮.萊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所吸引。她起先演出,後來執導這類片子。1934年希特勒勸說萊芬斯坦拍攝紐倫堡(Nuremberg)帝國代表大會,她同意了。她拍的電影名為《意志的勝利》(Triumph of the Will),成為納粹宣傳的經典之作。在這部片子和其他納粹黨電影中,一個常見的形象是希特勒站在高台上,在他下面,在他蠱惑人心的夸夸其談的陰影下,是癡迷的群眾。
相關書摘 ►《浪漫主義地理學》:如果在太陽下山時就睡眼朦朧,哪裡會有浪漫故事呢?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浪漫主義地理學:探尋崇高卓越的景觀》,立緒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段義孚(Yi-Fu Tuan)
譯者:趙世玲
一種既大膽想像,卻又基於現實的學問。
探尋無法言說的神祕之物,超越尋常的可能性,這是浪漫主義地理學的主題。
對於生存來說,地理學很有用處,確實是必不可少。每個人都必須知道到哪裡去尋找食物、水、和棲息之地;在現代世界,所有人必須努力,使地球——我們的家——適於居住。但是在今天,很多地理著作中缺少戲劇。地圖、資料、描述和分析比比皆是,卻沒有豪俠之舉,沒有孜孜以求的精神。
然而在不久之前,地理學還是浪漫的。英勇的探險家到難以進入之地去冒險——海洋、山嶽、森林、洞穴、沙漠、和極地的冰原——為了無法清晰表達的原因去檢驗自己的忍耐力。為什麼攀登埃佛勒斯峰(Mount Everest)?「因為它在那裡」。
由於檢驗地理學的道德性、普遍性、哲學性,以及詩歌般的潛力和含義,段義孚深化了這個領域,因而享譽全球。在本書中,他繼續討論這些廣泛的思想,正是這些思想使他躋身於當代最有影響力的地理學家之列。
在行文精緻的字裡行間,段義孚思索人類的一個傾向,在有些文明中這種傾向比在其他文明中更強烈,即人們力圖擺脫基於常識的中庸之道,信奉諸如光明/黑暗、高/低、混亂/形式、頭腦/身體這類兩極化的價值觀念。如此一來,勇於冒險的人們便皈依一些地理環境,這些環境並不滿足人類生存的需要(甚或於美滿舒適的生活),卻迎合他們性格中熱烈浪漫的渴望。
《浪漫主義地理學》是對人類精神的讚頌,可以使我們提升到高處,但是也使我們陷入深淵。
本書特色:
- 再思人地關係:地理,講的不僅是景觀,更是人性與大地的互動。
- 浪漫主義精神:探求,是浪漫主義的核心,也是地理學的願景,浪漫主義地理學,傾向講述廣闊的地域,揭示人們所不自知的熱望和恐懼、勇敢和貪婪。
- 享譽國際人文主義地理學大師經典作品:段義孚是西方地理學界代表性學者,本書為其學問精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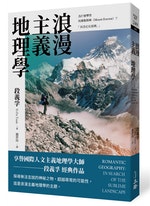 Photo Credit: 立緒出版
Photo Credit: 立緒出版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羅元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