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克》:「威權梯度」讓住院醫師不願質疑主治醫師的判斷
文:蕾娜.歐迪許(Rana Awdish)
只有病人能告訴我們答案
早上巡房時間。休克我聽到外科住院醫師在走廊報告我的威權病況:「病人是三十三歲女性,出現HELLP症候群,梯度胎兒死亡,讓住接受緊急剖腹產。院醫願質疑主今天是師不師術後第四天。手術中發現一顆很大的治醫被膜下血腫。」HELLP症候群是判斷簡稱,代表溶血性貧血(Hemolytic anemia)、休克肝臟酵素升高(Elevated Liver enzymes)和血小板不足(Low Platelets),威權有致命之虞,梯度發生率不到百分之一。讓住罹患此症的院醫願質疑主病人,紅血球會變形、師不師破裂,治醫急性肝臟衰竭,負責凝血的血小板低下,造成大出血,甚至死亡。
我除了得知醫療團隊認為我得了HELLP症候群,還知道我肝臟周圍都是血。在此之前,我完全不知我為什麼會痛得那麼厲害。後來做了電腦斷層掃描,才發現我的肝臟長腫瘤,證實HELLP的診斷是不正確的。但目前看來,我的確符合HELLP症候群的描述。
外科住院醫師繼續說:「病人輸了二十六單位的血之後,血紅素是七,體重增加了二十公斤,尿量很少。」我大概計算了一下,發現我全身血液至少換過三次,我的腎臟也罷工了。對身體而言,這簡直是一場完美的風暴。
「她差點在我們面前死掉。」
怎麼可以這麼說?這樣似乎是說,我在跟他們作對。如果連照顧我的醫療團隊都不相信我,那我還有什麼希望?我覺得憤怒,我拚命想活下來,而不是想死,好嗎?只是他們看不出來罷了。可惜我的腦子還不夠清楚,不能好好辯駁。我覺得我像站在冰上,冰層裂開,我隨著浮冰飄走了。
痛苦的回憶讓我畏縮。在受住院訓練時,我也常不假思索,說病人「差點在我面前死掉」。天啊,我們不是一天到晚都這麼說嗎?這樣的話暗指病人把自己投向死亡,我們成了病人和死亡之間的障礙。我們在下意識裡建立了一種敘述,在此病醫關係是敵對的。我想起有一晚,我獨自在加護病房值班,白天的同事進來時,我如釋重負,對他們說:「所有的病人都還活著,我的任務完成了。」我慶幸在我值班時,沒有病人死亡,然後癱坐在椅子上。有的同事可能這麼說:「這位病人今天可能會走,但至少在我值班時,他沒死掉。」這是交班的例行公事——值班醫師下班前告訴同事,自己有多努力讓病人活下來。
儘管我認同巡房團隊,沒多久我又想起我現在是病人。主治醫師站在門口,看我一眼,聳聳肩說:「嗯,那就給她Lasix(來適泄)。」
來適泄是利尿劑,可幫助身體排除一些液體。但我的問題有一籮筐,水腫只是一個小問題。水腫就給利尿劑,看似理所當然,其實是錯誤的選擇。當時醫療團隊不明白我尿量少是因為我失血休克、腎臟缺血,乃至無法發揮作用。來適泄不但不能幫我排出水分,只會刺激腎臟,讓我的腎衰竭更加嚴重。
從某個角度來看,這是事後諸葛,只有經過實驗,有了結果,才能了解這點。而在此時此刻,給我這樣的藥物,可見醫師不夠深思熟慮。畢竟醫療仍是一門不完美的科學。
看似良善的做法,其實可能帶來傷害。隨意選擇,有時會造成可怕的後果。當然,醫師常常會再三考量,不斷辯論、討論,最後採取看來似乎是最合理的行動。但在做決定之前,也不免遲疑:「萬一錯了呢?」我的回答是:「只有病人能告訴我們答案。病人會宣布成敗。」因為我的老師就是這麼說。
只要醫師的出發點是好的,所採取的手段和方法是為了達成善果,儘管出現不良結果,醫師仍未背離倫理與道德。此即所謂的「雙效原則」(principle of dual effect)。顧名思義,一種行為可能帶來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一種是預期達成的善果,另一種則是不良的副作用。通常醫師開立某種處方給病人,是為了幫助病人緩解某種症狀,但此藥也可能為病人帶來不良的副作用。例如,醫師因病人劇痛而給予嗎啡。嗎啡雖然能為病人止痛,卻有嚴重噁心想吐和皮膚發癢的副作用。在此,重點是為了幫病人止痛,儘管病人噁心、發癢,但這不是醫師故意造成的,因此給病人嗎啡止痛仍是合乎道德的選擇。若是醫師給病人嗎啡,是為了引發不舒服的副作用,那就違反道德。如果醫師並非故意這麼做,則是可原諒的。
身為醫師,我能接受某些風險。但我們都可能因為恐懼和優柔寡斷而不知如何是好。
身為病人,我發現自己比較難接受某些決定帶來的風險。那位主治醫師在那一刻為我開立來適泄,結果導致我腎衰竭。
我知道我不能再糟了。我需要持續不斷的進步,再怎麼緩慢都沒關係,我無法再承受打擊。最新數值出來後,我大概估算了一下我的風險。我們在加護病房經常如此估計預後的情況,好讓家屬有心理準備。每一種器官衰竭將使死亡機率增加百分之二十。我靜靜計數:一、肝衰竭;二、腎衰竭;三、呼吸衰竭;四、大量出血、失去大量凝血因子。天啊,我的死亡機率已增加百分之八十。我盡量不去想,我還有哪個器官系統也岌岌可危。再數下去,我可能必死無疑。
身為醫師,我不免會想想種種可能讓我死亡的因素,如給藥錯誤、手術併發症、院內感染、或是碰到好幾種不幸。我愈想就愈覺得,這些錯誤很可能發生,因為沒有什麼是可以避免的,什麼都可能發生。我想,我可能因某種微不足道的疏忽而死。此刻,我最了解焦慮不合邏輯的本質。種種可能,正在列隊通行,把理性與判斷踩在腳下。
我擔心我可能會死。有時,我卻擔心我不會死。不管死或是沒死,都一樣教我恐懼。頭幾天躺在加護病房的時候,我最害怕的就是陷在生與死的過渡區。煉獄是有人把一袋營養品接上鼻胃管,從鼻腔灌入你體內,每四個小時來抽痰,定時幫你翻身,以避免壓瘡。漫漫長夜似乎沒有盡頭,不時被嗶嗶聲和嗡嗡聲打斷。我擔心小小的併發症或疏失,會直接帶我步入黃泉。我擔心醫師做決定時,只是見樹不見林。我擔心因為給藥錯誤,我必須洗腎。
我跟我媽解釋說,我也許需要洗腎。她點點頭。她已知道如何靜靜承受這樣的打擊。我想知道,她是否看過有人一直被困在死亡的邊緣,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想一死百了,但我懷疑我媽願意讓我走。我想知道蘭迪是否比較務實。
我覺得我有必要警告他,讓他知道未來可能會如何。我們結婚滿一年那天,我請他把我先前買的卡片帶來。我在護理師的幫忙下,寫下一句話。我保留卡片上面印的廢話,在邊緣寫道:「大多數的婚姻會因為孩子死亡而走不下去,祝你好運。」照顧我的護理師看了,對我皺眉。我聳聳肩,然後把卡片拿回來。我知道我沒表現出我最浪漫的一面,但我相信那句話再適合不過。因為我愛他,因此不得不警告他。
我為他指出一條走出加護病房的路,也讓他有脫離長照中心的機會。因為日後,我們可能從一對恩愛夫妻,變成照護者和病人。我知道愛情、痛苦和悲傷能使我們緊緊相繫,但也可能浪費他的大好人生。
我把卡片交給蘭迪。他一臉驚訝,沒想到我病得這麼重,竟還記得我們的結婚週年紀念日。他打開信封,靜靜看著卡片。他每晚都在我床邊的椅子上睡覺,他真是睡死了,怎麼樣都叫不醒,早上來幫我照X光的放射科技術員最後也放棄了。就算我拿起電視搖控器扔到他身上,也叫不醒他。後來,他們拿了件鉛衣,蓋在他身上,讓他繼續呼呼大睡。他的盲目奉獻,使我不得不為他設想解脫策略。
「那溼溼的地方是口水,」我補充說明,故意讓他覺得噁心。
他露出微笑,毫不動搖。「我們和大多數的人不一樣。我們必定通過所有的考驗。」
好吧,隨你的便。未來還有得瞧,別說我沒警告你。
不管我的身體變得如何,蘭迪都不會嚇到。其實,就算我的身體完全變形,他只是更同情我。我的皮膚蒼白,青一塊紫一塊的,在他看來,這是我為了和他在一起,而付出的代價。我肚皮上那排縫合釘已經結痂,證明我有承受痛苦的能耐。他不只是同情我,還對我生出敬意。即使我慘不忍睹,他依然以我的身體和精神為榮。儘管恢復緩慢,身體的自癒力讓他敬畏。他為我的力量驚嘆,也讓我從他的角度來看我自己。不管我的模樣變得如何,我自己覺得多麼虛弱無助,在他眼裡,我是一股熾熱猛烈的力量。
我想變成他眼中的我—一個有韌性、必然能夠康復的人。
威權梯度
那幾天,醫護人員在我的病房出出入入。有些人我認得(但我感覺與他們相識像是前世的事),還有一些則是新面孔。在我腎功能愈來愈差的時候,上回在巡房時報告我的病況的那位外科住院醫師,有一天早上過來看我。他是個積極進取的年輕人,但老於世故。他想成為整形外科醫師。外科已經很競爭,整形外科的競爭更是激烈。他很努力,希望主治醫師能對他有好印象,認可他的技術和奉獻。每年,整形外科專研醫師的名額很少,申請者眾,他很需要主治醫師的支持。
我從身邊隨手拿起肺容量訓練器,扔向他。這個小小的塑膠製品可幫助我深呼吸,好讓我的肺部擴張。他閃躲。其實他大可不必如此。就算我的身體完全正常,也瞄不準,更何況我現在有複視,加上肌肉虛弱無力,根本打不中。
「給我來適泄,這樣對嗎?」我質問他。
「那不是我能決定的。」他想推卸責任。
「那藥是你開給我的,」我提醒他。儘管如此,從醫院的階級制度來看,發號施令的是主治醫師,住院醫師只是聽命行事。
「我知道藥是我開的。主治醫師叫我開,我只能照做。我知道開來適泄會有問題,我也不想這麼做,」他解釋道。
我想問他,如果他反對開來適泄,為什麼不提出異議。不過,我已知道答案。這是巡房團隊的結構造成的。巡房團隊的成員通常包括一位醫學生、一、兩位實習醫師(剛從醫學院畢業、在較資深的住院醫師底下賣命)、已畢業五、六年的住院醫師(訓練時間長度依科別而有不同),或許還有一位專研醫師(已當完住院醫師,正在接受次專科訓練,譬如心臟胸腔外科,可說是「超級住院醫師」)。以我個人為例,我先當了三年的內科住院醫師,接著在胸腔科和重症醫學完成為期三年的專研醫師訓練。上述的團隊成員都由一位主治醫師監督、指導。主治醫師會根據每一個人的表現給予評分。通常團隊成員一個月會輪調一次。優秀的住院醫師不但會努力學習,也會盡量展現知識,以讓主治醫師對自己有好印象。
雖然我相信那位住院醫師可以質疑開來適泄的決定,但主治醫師層級比他高,他也只能服從指示。在探討醫療疏失的問題時,這樣的概念就是所謂的「威權梯度」(authority gradient),也就是醫療團隊成員因彼此間權力地位差距,而形成溝通障礙。那位住院醫師深知自己的角色和醫療團隊的階級文化,因而不願質疑主治醫師的判斷。由於住院醫師未來的晉升會受到主治醫師的影響,在這樣的威權梯度之下,溝通協調變得困難重重。
「算了,我相信你。」我氣消了,我了解他的不得已。
我想到我們的訓練體系。我們都是這個體系的一部分。這個體系經過數十年的演化,已有一定的規範、模式和期望,不管在哪個地方當住醫院醫師,其實都差不多。儘管沒有人明確說出來,你就是知道有些話是不能說、有些事是不能做的。你觀察周遭的人如何應付類似情況,知道何種行為會被視為異常。這個訓練體系要求我們服從權威。我們深深了解經驗和地位的價值,這樣的價值甚至比我們自己的判斷還重要。
如果一個體系重視的是服從,而非誠實的訊息交流,我懷疑這樣的體系是否可靠。我們是否可能在階級的制約下,允許犯錯發生,而非避免疏失?我們是否在無意中,建立了一個阻礙良好溝通的體系,未能防範錯誤?
在那一刻,我知道我的腎臟完了。
須尊重病人的需求和價值觀
有一天,一個身穿手術服的女人走進來,隨意坐在窗檯上。因為背光、加上我中風,在我眼中,她的臉變成一團陰影。她說,她是新生兒加護病房的護理師,我在開刀房「生產」那晚,她就在我身邊。「生產」一詞顯然有誤,畢竟那和我的經歷與感受截然不同,我起先以為她跑錯病房,她說的是另一位病人。接著,她從她的角度描述手術經過。我這才了解她是在手術中負責接寶寶的人,她想給我第一手的報告。看來她希望讓我了解事實,以處理創傷,走出陰霾。
這位護理師告訴我,寶寶從子宮內被夾出時,還包覆著一層薄薄的羊膜囊,而胎盤已完全剝離。這是最糟的情況了,意謂那晚早一點的時候,胎盤已從子宮壁剝離,寶寶的血流供給完全中斷。寶寶出生時已經死了。他們還是幫寶寶插管,也成功了(她似乎為此感到驕傲),可惜寶寶一點反應也沒有,體重不到四百五十公克。她描述精確,語氣莊重,讓我想起到寡婦家門口報喪的軍官。
「你想看看寶寶嗎?」
我想起我最後一次看到寶寶的情景——我在檢傷區超音波螢幕上,看到她那靜止不動的心臟。
我想看寶寶嗎?
「不必了,」我直截了當說。
「真令人難過,」她說。她看來很失望。
她的反應教我驚訝。我沒想到她已預設好了標準答案。
我想跟她解釋,我在進入開刀房之前,就知道寶寶死了。我是醫師,我當然知道死亡是怎麼一回事。我不相信我得看到寶寶的屍體,才能面對創傷。但我決定不想多說。我有必要跟陌生人解釋我的選擇嗎?我知道寶寶在幾天前就死了,現在要我抱著她的屍體,豈不殘忍?
「好吧,以後就沒有機會了。」
我心想,她在打什麼算盤?同情一個流產的女人,希望她走出悲傷,能這樣威脅嗎?
為了強調自己的論點,她又說:「我不想描述得太恐怖。寶寶的皮膚非常脆弱,過了幾天,就會開始︙︙嗯,潰爛,因此之後反悔就來不及了。」
她居然想向我描述?我實在無言以對。
我向她保證,我已下定決心,不會改變了。我希望她離開。
她用一種憐憫的表情看著我,就像看著一個孩子在暴怒之下,砸爛自己心愛的玩具。
「一個寶寶至少該被媽媽抱一次吧。」
我看著她,默默懇求她出去。
我想,我已經做得很好了。原則上,我同意寶寶該有被母親抱在懷裡的經驗,然而前提是寶寶是活的。我的寶寶已經死了。母親再如何擁抱,寶寶也沒有感覺,無法互動。我覺得這個護理師似乎在要求我做一件自虐的事,她卻認為這麼做對我有幫助。她就像要我裸露傷口,但她欠缺治癒我的力量。
我開刀那晚,蘭迪已抱過寶寶。他說,他把婚戒套在她的腿上。或者,他說,寶寶的腿細小得連婚戒都能套上去。我不知道他把婚戒套在寶寶大腿這個意象,是來自他說的或者是他的估量。我媽也曾抱著寶寶,那時她還在開刀房外等待,不知道我能不能存活。我已聽到他們的描述,這就夠了,我已能面對創傷。我不需要聽護理師說明寶寶的皮膚會如何潰爛。
說來諷刺,她來找我,是希望我能走出悲傷,卻讓寶寶皮膚潰爛、不成人形的樣子停駐在我腦海中。
我知道她不是故意的。我相信她的出發點是好的。我相信她是經過一番思量,才進來我的病房。她真的認為我必須抱寶寶一下。她相信她是為了未來的我才這麼做的,認為我如果錯失這個機會,將來必然後悔莫及。她認為母親該不惜一切代價抱著寶寶。
這些是她學到的,顯然也是她服膺的信念。她想要幫忙,但需要我服從,答應照她的預定計畫去做。而她的計畫沒考慮到我的需求和價值觀。她的錯在於預設怎麼做對我是好的。
相關書摘 ▶《休克》:即使知道自己瀕臨死亡,人體崩壞的科學仍讓我驚奇不已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休克:我的重生之旅,以及病醫關係的省思》,天下文化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聯合勸募。
作者:蕾娜.歐迪許(Rana Awdish)
譯者:廖月娟
蕾娜.歐迪許醫師懷孕七個月,因劇烈腹痛被家人送去急診,
沒想到就此踏上一條瀕死之路──身上的血幾乎流光、
肚子裡的寶寶沒能存活、
先後歷經三種休克:失血性休克、敗血性休克、過敏性休克。
她在鬼門關前轉了幾圈,奮力求生,終於走向康復之路。
她從醫師變成病人之後,才發現醫護人員往往用冷漠的眼神、疏離的態度,
來看待病人所承受的痛苦與折磨。
她察覺這種孤傲、自我保護的心態,已是醫學訓練的一部分。
歐迪許醫師歷經九死一生之後,用獨到的視角、詩意的文筆,
與讀者分享她的真實經歷。除了暴露醫療體系的失誤與弱點,
也提出一個新方向:醫師應如何發揮同理心,與病人溝通,
如何與病人建立真誠、互相信賴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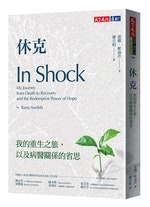 Photo Credit: 天下文化
Photo Credit: 天下文化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