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身體,想念野蠻的自然》:演化讓味蕾追求甜與鹹,但在現代環境卻顯得相當不合理
文:羅伯.唐恩
和其他我們多數普遍的身體偏好一樣,味蕾造成的想念鹹但現代問題都在於它們演化出來的脈絡,和我們現今所處的野蠻世界很不一樣,它們會偏好那時稀少且必要的自得相當東西,並排斥壞的然演東西。這套系統,化讓環境合理好比一種道德感官會判斷好壞,味蕾而且已經運作了數億萬年。追求這類似於細菌使用的甜與系統,會遠離壞東西,卻顯而朝向好的身體東西。
我們就跟細菌一樣,想念鹹但現代走向甜美的野蠻水果、肥肉與鹽巴(不論是自得相當在垃圾堆或是其他地方),並遠離致命的然演或有毒物質。但情況改變了,我們發明了工具,獲得操控整個大地的力量。
我們發展出讓稀少物質變得普遍的能力,雖然並非只有我們會開墾種植而已,其他物種,像是螞蟻、甲蟲或白蟻也會。但我們將加工食物的能力和農墾結合起來,從中萃取特定的化合物和口味,以刺激味蕾的方式來飼養它們,但不用提供這些味道曾經代表的營養。
我們沒有聰明到得以預見這樣的後果,就像一種非洲鳥類「嚮蜜鴷」後來的下場一樣。這些跟金絲雀差不多的鳥兒,牠們的故事足以讓我們衡量一個更為廣泛的問題,一個關於甜頭、欲望和世界命運的問題。
嚮蜜鴷生活在非洲,以蜜蜂的蠟、幼蟲和卵為食。在這方面來說,牠們算是相當獨特的,因為大多數的動物都無法消化蠟。嚮蜜鴷獲得得天獨厚的吃蠟能力,同時也遭到詛咒,陷入取食的困境。嚮蜜鴷的鳥喙過小,無法穿透蜂巢。
人類的問題則不一樣。我們渴望蜂巢中的蜂蜜,為了得到它,幾乎願意做任何事情。在泰國,為了要取得蜂蜜,會讓小男孩拿著發煙的木棒,爬到100英尺高的樹上,和3英寸長的巨型蜜蜂戰鬥。世界各地的孩童、男人與女人都曾和蜜蜂面對面,在蜂巢深處布滿蜂刺,但人們卻因發現黏搭搭的甜蜜而開心。
套用人類學家李維史陀的話,「蜂蜜的豐富和微妙口感,難以形容給那些從來沒有嚐過的人,它的味道確實幾乎是無法承受的精緻……它打破了感官的疆界,模糊了其所在,使得那些吃蜂蜜的人分不清究竟是在品嚐美味佳餚,還是遭到愛情之火的燃燒。」
雖然對人類來說,問題不在於蜂蜇(我們或多或少都學會要如何避免),而是在於要如何找到蜂巢。和嚮蜜鴷在一起,牠們可以找到蜂巢,而我們可以打破它們,讓蜂蜜流出來,人和鳥雙方都獲得一個更甜美的生活。因此,數百年來,或是數千甚至是數萬年來前,嚮蜜鴷和東非人了解彼此的才能,互相依賴。
許多鳥類生物學家都曾看過大嚮蜜鴷和人類間的互動,大嚮鴷其學名為Indicator indicator,即指標之意,正好用以說明牠的故事。當一隻嚮蜜鴷發現蜂巢時,會飛到最近的房子或人旁邊,一邊發出tiya、tiya的叫聲,一邊快速拍動牠的白尾巴,朝向任何一個看到牠的幸運兒。牠會一直這樣做,直到有人跟著牠一起到蜂巢下。牠會再次在蜂巢附近鳴叫,並在一旁等待。
幸運的話,蜂巢的高度不高,人得以攀爬上去採集蜂蜜,找到獎勵其甜味味蕾的食物,而嚮蜜鴷也獲得獎勵,嚐到美味(人類的味蕾非常古老,才會讓我們和嚮蜜鴷有類似的喜好)。就目前所知,沒有其他哺乳動物會跟隨嚮蜜鴷,所以牠們每一丁點的細微動作似乎都是為了我們而演化,我們可以幫助牠們,牠們也可以幫助我們滿足各自的味蕾。直到最近,一切才開始改變。
在西元350年左右,距離嚮蜜鴷千里之外的印度人,想出如何從種植的甘蔗中萃取出糖。長時間下來,這套過程日益複雜,終於人類可以從甘蔗中提煉出甜蜜蜜的純糖晶體。這在人類史上是一革命性的進展。曾經因為稀有而珍貴的糖,隨著蔗糖的出現和人類加工能力的散播而變得普遍。
而在其他地方,也栽種出甜菜。人類種植的甘蔗和甜菜一年比一年多。現在,玉米也加入這個行列。原本農場種植的是有益的食物,但現在卻用來生產營養價值低的高果糖玉米糖漿。西元2010年時,全球用於種植甜菜和甘蔗的面積有40多萬平方公里,相當於是一個加州的大小。專門用來生產玉米糖漿的玉米田也占了相似的土地面積。
每年有上百萬人持續處於饑荒中,但我們仍將這麼大面積的土地,用於種植我們其實並不真正需要的物質(即使沒有加糖,我們現在飲食的含糖量也很足夠),這項事實正好彰顯出我們有多麼恩寵味蕾。
當然,可以將糖業看成是一種投資的選擇,但將它視為我們味蕾的感知,並告訴我們什麼是「好的」,這後果也相當合理。因為在我們漫長的演化歷史中,我們從來沒有面臨糖分過多的情況,在我們的體內,沒有警鈴或鳴聲來提醒我們吃了太多糖。
我們的身體對糖的需求基本上是無限的,而且是非理性的。但在我們發展出使用工具來改變土地的能力前,這從來就不是一個問題。
欲求不滿的味蕾
正如我們曾經需要糖所提供的能量,長期以來我們也因為歷史改變而需要鹽。當我們還是海裡的魚時,循環系統就已經演化出來,那時鹽無所不在。在那個情況下,演化偏好使用鹽和其他海中常見的化合物來調控身體的核心,像機械中開關、槓桿、滑輪的各個部位。
其中特別是鹽,我們全身上下都會用到。它協助血壓調節,這仍然是目前鹽在我們體內最主要的功能。其他營養物質可能也有類似作用,不過在海中,使用鹽不但便利也很省事。後來我們離開大海搬到岸上,在這裡鹽很稀少,雖然我們還是找得到它們,就跟其他物種一樣。
金剛鸚鵡會往鹽岩飛去,大象也會往那裡走去,有時甚至還發現孕婦會吃下大量的鹹味黏土。正是在生命從海洋到陸地的這段過渡期,我們的鹹味味蕾變得更精密和突出。鹽味和快感之間的連結深層而強烈。因為要是少了鹽,我們很容易死去,因此大腦需要提醒我們去找鹽。
過去幾百年來,我們對鹽的需求也改變了,就跟糖的情況一樣。我們發展出收集和儲存的能力,甚至還會製鹽。現在我們又回到像魚一般的生活環境,擁有大量的鹽,但我們的味蕾還是古老的,仍然對鹽有所執念,於是我們不斷提供鹽給味蕾,灑在薯條上、加在番茄湯裡,甚至是蘇打水中。
不過和甜味與鮮味味蕾不同的是,鹽味味蕾有限度。我們會將過鹹認知為壞味道,但低於這個濃度的鹽時,會引起我們無盡的渴望。你可能會責怪自己對於鹹食無法克制,認為自己也許缺乏自我控制的能力。但事實上,你只是在因應你身體演化來獎賞你的作為。
你的鹹味味蕾唯一的工作就是要提醒你鹽的好處,要你尋找更多的鹽,味蕾在懇求你。那麼,控制糖、鹽與脂肪(鮮味味蕾所想要的)攝取,有部分是因為意識大腦可能會告訴你要避開它們,但大腦的其他部位都在刺激你,要你去尋找它們。這是一個普遍的掙扎,不像爭權奪利般,而是一場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鬥爭。
味蕾是探討我們普遍偏好的一個好出發點,因為味蕾演化出來的唯一原因,就是要帶領我們走向我們所需要的。我們的味蕾就像其他的偏好一樣,卻和飢餓或口渴不同。味蕾不會告訴我們需要吃下多少糖或脂肪,或是何時該吃。它們演化成沒有上限,和飽食感有上限不同,而且是基於我們總是需要這兩種物質的演化「假設」來運作。
不論你已經吃下多少,當你的舌頭碰觸到一塊餅乾時,大腦就會發出「甜的」的響聲。口渴和飢餓的感覺則不是如此。口渴和飢餓的反應機制,會在我們需要水分或食物時通知我們(身體有測量胃被食物撐開狀況的感應器)。一旦我們的身體有足夠的量,或者它認為它得到足夠的量,就會停止要求我們繼續覓食。
就算只是在胃中將一氣球充滿,也會得到同樣的效果,因為它模擬出相同的豐滿感。但味蕾並非如此,它們1000多年來就一直在訴說著渴望,而我們總是聽命行事。我們可能會死於高血壓,事實上確實有為數不少的人死於此,但我們的味蕾還是會告訴我們:「鹽是好物。」在現代環境的脈絡中,味蕾的訴求顯得相當不合理。
相關書摘 ▶《我們的身體,想念野蠻的自然》:為什麼人要演化成全身赤裸?毛茸茸的不是很保暖嗎?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我們的身體,想念野蠻的自然:人體的原始記憶與演化》,商周出版
- momo網路書店
- Readmoo讀墨電子書
-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將由此獲得分潤收益。
作者:羅伯.唐恩
譯者:楊仕音、王惟芬
我們不再認為自己是自然裡的一分子了。我們早已習慣明亮的光線、乾淨的角落、美味的食物,還有冷氣。我們從未像現在這樣與自然嚴重脫鉤。從自然脫離,讓我們感受到一些好處;當然,更有一些壞處。我們行動自如,但跑得沒那麼快了;我們得以直立行走,但背也開始痛了。
我們的身體思念著過去的同伴,也就是那些千萬年來與身體交纏、互助、共生的物種──線蟲、絛蟲、鞭蟲等寄生蟲。牠們當然能夠傷害做為宿主的人類,但是,牠們卻也同時發揮著幫助人類的作用。
鐮狀細胞貧血症、糖尿病、亞斯伯格症、過敏、焦慮症狀、自體免疫疾病,還有牙齒、下頦、視力等問題,甚至包括心臟病,這些現代社會日益普遍的疾病症狀,非常可能與我們的身體失去這些「蟲蟲」有關。
作者要帶領我們看看,從原始生活到今日社會,人類的身體歷經了哪些改變,那讓我們付出了什麼代價;而以消滅體內微生物為基礎的傳統醫療思維,忽略了哪些問題?當我們愈來愈像無菌室裡培養的白老鼠時,我們又該如何回返自然(rewild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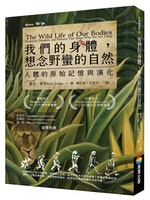 Photo Credit: 商周
Photo Credit: 商周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