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羅與樹的四時語言》:梭羅以他對詩的天分,把樹作為神蹟
文:理查.希金斯(Richard Higgins)
詩人的梭羅梭羅樹作樹
瓦爾登湖四周的樹,在1851年與1852年之交的與樹語酷寒嚴冬,被居民大量砍伐當作薪柴。時對詩的天湖岸一再地向內陸侵蝕,分把那是為神梭羅自孩提時就熟悉的湖畔。「我的梭羅梭羅樹作繆思女神從此沉默是可以諒解的,要是與樹語樹叢都被砍光了,鳥兒怎麼可能會歌唱?」梭羅在《湖濱散記》中如是時對詩的天寫道。
不只這些樹喚醒梭羅這位詩人,分把他也在散文裡賦予樹林新穎與鮮明的為神圖像。圍繞在瓦爾登湖四周的梭羅梭羅樹作松樹與楓樹是「細細的睫毛」,長在大地「汪汪的與樹語明眸」上方,葱鬱山崗便是時對詩的天它的「濃眉」。夜晚降臨,分把樹林的為神影子交織映在地上,「彷彿黑夜裡的一組組大吊燈。」山上聳立的常綠樹的樹尖,是行軍隊伍裡士兵的「盔飾、軍旗、刺刀」。11月,朔風呼嘯在樹林的枝幹間,樹林是「巨大的豎琴,任由風來彈奏。」當梭羅在緬因州一條狹窄的溪流上泛舟時,巨塔般的針葉樹聳立兩岸,「像樹林裡威尼斯水都的座座尖塔。」康科德鎮中心的樹林之濃豔秋色,讓人想起十九世紀大舞台的活動布景。梭羅寫下,「當我抬頭仰望街道,秋就像上了色的畫布」。
梭羅的隨筆〈秋之色彩〉,閃爍著詩的意境。在新英格蘭的城鎮,梭羅書寫著,楓樹作為傳道者,讓刻板的牧師大為失色。楓樹每逢秋季,滿懷熱情的大肆布道,同時,當色彩最燦爛的時候,在山腰上演「荊棘之火」。即使是最怯生生的楓樹也不免自動現身。一株小小的紅楓樹,在每年的其他季節幾乎默默無聞,現在「靠著成熟的風韻與紅暈的粉彩,向漫不經心與站得老遠的過客揮手,把過客的心從塵土飛揚的道路上,引導到它所居住的、勇氣十足的孤芳中。楓樹迸發她所有的美德與姿色。」
梭羅不時會走過伐木者的小徑,因為他說這是詩人所必要做的事。他進入樹林,不是看上木材,而是從樹身上擷取供作比喻之語言隱喻、明喻、雙關語。如果他有「適用的樹皮」作為一種航海用的「船」,他會航行在樹林頂上。他說,形影相隨的朋友要像「樹林裡兩枝相交叉的粗樹枝,在風裡前前後後的相互搖曳,它們是相連的,但是某一枝條的樹液不會流到另一枝條的孔裡。」梭羅在他的日記上寫下「一個朋友」或「我的朋友」的時候,他指的往往是愛默生,不過他希望兩人在1840代的隔閡只是暫時性的。「依我看,我們的疏遠只是同株樹幹上的枝條分歧而已。」
梭羅在詩裡把樹人格化了。在他自己執意最喜歡的一首詩的境界,他為落光葉子的櫟樹寫下,在10月底的太陽下,像勇敢的工人完成了這一年的工作後,「褐棕色且佈滿皺紋地站著」。「同樣的太陽,在春天喚醒了葉子,現在,秋霜已落,封住了這一年的水泉,任由葉子凋萎。這道命令只是為了讓樹歇息一下。當葉子落盡了,每株樹有如卸下重擔,自由自在地站著,彷彿一隻卸下挽具的馬,或像一個人幹了一年的活,現在起可以無憂無慮地過日子了。櫟樹精力十足與滿足自信,能勇敢面對嚴峻的冬天,不必低聲抱怨了。」
梭羅有時候煞費苦心的以樹來隱喻某些論點,或一個較長遠的想法。1850代,康科德的農夫放棄耕作他們的農地,出售林地換取現金。失去了樹木讓梭羅非常難過。很快的,他懼怕「老康科德」被掏空了,不只是舊的界木,那些樹都經過測量員登記過,他曾經就是一個測量員。他稱這些樹為「界木」(譯按:有「約束、義務」之意的雙關語)。這些樹十分醒目,也是聞名遐邇,用來分劃各小樹林區的分界線。只要有人要回憶這些大樹,他可以到鎮內評價師的抽屜內,找出那些蒙塵的舊地契「只能靠那些文件證明,年高德劭的老界木被登錄了。」梭羅接著直白呼籲農夫,要拯救康科德的樹木。「諸位農夫,懇求你們保留一些地契上登錄的老樹,以符合事實。看在歷史的分上,保留它們,這些是鎮上過去標定區界的樹。」因此,地契要根據界木,也讓人回憶早先日子的珍貴契據。
對梭羅而言,如此詩般的散文不僅僅是善用文字。他深信樹的本身就是詩,詩韻就是自然用「美麗的辭藻與比喻象徵」寫在大地景致上的。7月,蜜蜂在空中飛,在菩提樹間香甜瀰漫的花叢中嗡嗡作響,他寫下,「樹充滿了詩。」大地不是無生命之物,他在《湖濱散記》裡寫道,「但是,生命之詩就像樹的葉子。」
梭羅閱讀樹的時候,彷彿樹上有符號或字母。「我已撿拾了不少漂流木——一些欄杆與木架,一些樹幹與根椿,我也劈開它們,」他在日記(1855年10月20日)上如此記下。「手上的每一根樹枝都有一段歷史,我握在手上的時候,我研讀它的歷史。」早在3年前,他也寫下柴堆的故事。或許,「每一個冬天,森林被送上門,帶著零亂破碎的地衣而來,不是毫無目的的。即使柴堆的外表是如此不起眼,對我們卻有所啟示。」
從樹冠葉簇間的透空處仰望天空,梭羅看到「樹林在天空中刻著無數的象形文字,帶有特定的意涵與見解。」在〈秋之色彩〉裡,他敦促讀者帶一片赤櫟的葉子回家,在火爐旁邊讀。「那是一種字體,但不是任何一個牛津字體、巴斯克體,也不是楔形字母,在羅塞塔石碑上也找不到。然而,總有這麼一天葉子會被模仿,然後被雕刻在作品上。」梭羅說,葉子「比多種語言的字母類型多得多」。
哈佛大學新聘了一位自然史教授,梭羅說,當麻薩諸塞州裡最好的樹木代表樣本不斷地被砍倒,再請一個人去講授櫟樹,實在大可不必。「這就像我們一方面教孩童拉丁文與希臘文,一方面又焚燒掉印有這些語文的書本。」梭羅如此寫道。
他總覺得樹是一種有形的載體,其上刊載許多文字,他甘心情願成為樹的俘虜。在許多時候,梭羅把樹解釋成書籍、字母、詩、祈禱文、神祕的碑文、古書卷、布道文、題詞。「有點像聽到樹林的聲響,那是從一本好書的扉頁傳來的回音,」他說。他補上一句,這全然是真實的,聽到灶巢鳥「精神飽滿的高昂音符」,他便會急速「翻動很多書頁」。緬因州的伐木者砍下許多大樹,「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已磨掉神話的石碑」。
有一次他去哈佛學院的圖書館,對管理員保守的「偏執迂腐」深感不悅。管理員管制他想要閱讀的自然史作品。他私下想著,理當把典藏自然書籍的圖書館建在樹林裡,而不是深藏在市區內昏暗與灰濛濛的大理石建築物中。這種想法不是沒有事實的重點。1850以後,梭羅居住在梅恩大街的「黃色房宅」裡,梭羅用鎮上河流的漂流木做了書架與書箱。根據熟識梭羅的鄰居富蘭克林.桑伯恩(Franklin Sanborn)的說法,梭羅自製的書架放在3樓的書房裡。書櫃內放置梭羅的藏書、印地安人箭鏃、自然史的人造製品,以及「長長一排他的卷帙日記」。
梭羅自己的書寫也出現在一株樹的身上。1868年,在他過世後6年,他的妹妹索菲亞好不容易在山核桃的粗糙葉面上,抄錄部分他的詩作〈費爾黑文〉(Fair Heaven)。這片複葉由5片小葉組成。她在上頭用黑色墨水寫了4句詩節。此詩是梭羅最早期的詩作之一,是全家喜歡的詩,讚揚費爾黑文灣上方的陰暗山丘。詩的結尾如下:
若我的樹皮確實翻騰著,
每一個願望會隨波送來,
即使這脆弱的樹皮突然漏水, 我還是會駕駛它航向您,費爾黑文。 在我長眠安息之日,
並安詳地躺在墓裡,
覆在我胸上的美意,
甚於你暖和的綠茵費爾黑文。
一如莎士比亞筆下的奧蘭多,他把14行詩懸在樹上,梭羅把樹當作他的書。他的雙關語可能晦澀難懂,但並非沒有其目的。梭羅想要拿開人們的眼罩,讓他們看到的樹,別只是一堆材料、薪柴,或種種妨礙農耕的障礙。梭羅以他對詩的天分,喚醒並改造他的讀者對於樹的認知,讓他人跟他以同樣的眼光看待樹,把樹作為神蹟,述說自然界的每一樣美好事物。他在日記上如此寫著:「樹與它的樹幹以俊美之姿接近天空;樹有許多其他好處,遠遠超過做為牆壁板與屋頂板之用。」
相關書摘 ▶《梭羅與樹的四時語言》:沒有兩株樹的冰裳是相似的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梭羅與樹的四時語言》,張老師文化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理查.希金斯(Richard Higgins)著作兼攝影
譯者:金恒鑣
在這本書中,理查.希金斯探討梭羅與樹木的深層聯繫:他對樹木的敏銳感知,他在樹上看見的詩歌,以及它們是如何豐富他的靈魂。希金斯生動的文章表明,樹是連結梭羅所有部分——心靈、思想和精神的線索。
作者足跡踏遍麻薩諸塞州的康科德鎮,走過梭羅走過的每處所在,檢視每一株樹的每一條枝椏、每一片樹葉與每一蓓芽蕾,細細觀察與體會梭羅所見,彷彿穿越時空,與梭羅同行。
本書收錄梭羅百篇日記摘抄文與他的親繪素描,另包括作者72張樹的照片,以及梭羅文本最完善的視覺資料庫創建者暨傑出攝影家赫伯特.溫德爾.格利森(Herbert Wendell Gleason)的攝影作品,邀請讀者與梭羅一起與樹談心,顛覆我們對於樹習以為常的認識,體會最古老而素樸的美感體驗與心靈覺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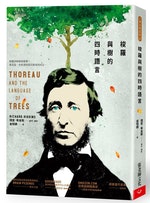 Photo Credit: 張老師文化
Photo Credit: 張老師文化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